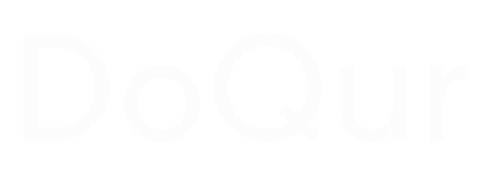很惋惜,這封寄給影片的情書沒能成功抄贈送給觀眾們
張藝謀在以往的影片中,常常用美感去開拓影片的攝影機詞彙,比如《红高粱》裡象徵強烈心靈衝擊力的黃色基調,《英雄》裡章節式美感化的運用,《影》裡中國畫藝術風格的黑白渲染等。
只好,2018年張藝謀給導演鄒靜之寫信說:“趁著我還能在荒漠上摸爬滾打,咱們抓緊把那個影片拍出來吧。”
2020年11月28日 刊| 總第2337期
除此之外,劉閨女這一配角也與張九聲實現了“母子”關係上的感情相連接,張九聲為劉閨女要來了做燈罩的膠捲,劉閨女為張九聲存了一年的“遺失物”。
影視製作獨舌 由新聞媒體人李星文創立的影視製作行業垂直新聞媒體。我們的五項新聞媒體主張:堅持原創,咬定專訪,變革文體,民間態度。
一名耄耋老人家穿著紅棉衣、拄著柺杖進了電影院;一名二八少女關上了厚厚的電影票夾,將《一秒钟》的票根放了進來……
只好,《我的父亲母亲》中觀眾們記住的人是“車馬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的唯美感情,《归来》中加強的則是“忘掉了你的臉孔仍舊不忘你的名字”的親情家庭。《一秒钟》的刀鋒仍然延宕著,但發展史缺位,感情顯得泛化,人物就不夠典型了。
2016年上海影片技術廠停用了生產膠捲的最後兩條生產線,這象徵著膠捲在中國的完結。跟歷史長河較之,它可能將很短暫,與幾秒鐘沒什么差異。但這么個“看影片”的故事情節,他不拍,也就沒人拍了。
這讓人不由得感慨,國師,你真的要把魂牽夢繞半生的故事情節,只寄給他們聽嗎?
技術有盡頭嗎?我不曉得。但表演藝術之路是沒盡頭的。張藝謀在絕大部分影片裡去探索“新”,結果為影片寫了箇舊情書。
電影在《英雄儿女》的放映中步入最高潮,沉浸其中的群眾大聲跟唱《英雄赞歌》,而張九聲正近乎癲狂地找尋遺失的劉閨女與“新聞簡報”。
【文/申兌兌】
張九聲(張譯 飾)“護”膠捲是為的是看兒子在影片之後“新聞簡報”中的幾秒鐘鏡頭;劉閨女(劉浩存 飾)“偷”膠捲是為的是補救哥哥弄壞的燈罩;範影片“救”膠捲是為的是挽回放映員的身分和眾人的擁護。
在追求“更多、更快、更新”的智能化時代,這些在心靈中驚豔過時光,又不動聲色離場的流光溢彩,我們有時候也想嘆一句,“幾秒鐘,不夠”。這就是《一秒钟》的象徵意義了。
其一,張九聲的兒子即使爭著當“先進”,在幹活時被面箱子砸死這一故事情節缺失了。這只不過是張九聲那個人物全數的行為動機。
一刪一增之間,營造了兩幅烏托邦式的幸福感情想像,以圖像縫合了苦痛敘事,以“個人化”視角拆解了宏闊發展史。電影給我們呈現出了一個希望中的結局,卻沒能給我們一個須要曉得的苦痛前史。
而劉閨女並非在搶膠捲的馬路上,就是在帶著膠捲逃的馬路上。她渾身上下都是戾氣,只有給哥哥往飯盒裡扒飯的這時候,就可以流露出一絲耐心和柔情。
電影最後添加的一年後的部份,張九聲發現劉閨女領到的並非兒子的兩截膠捲,自己三個再度跑進當初揮手告別的地方。張九聲胡亂踢翻沙漠上的沙,妄想一年前沖走在該處的膠捲能夠再現,但最終張九聲一個“鼻子蹲兒”倒在了沙堆裡,他和劉閨女相互看著傻笑。
而且,《一秒钟》哪裡是表達愛的情書啊,它分明是一個老小孩掏出的童真時期彌足珍貴的江湖祕籍。當人家告訴他這是核武器時代,他笑著擺了擺手,我就想他們備考一遍,你們願意看一眼也行。
在正式公映的四天前, 繼《一秒钟》因“技術其原因”維也納影展臨時撤映後,又錯過了金雞獎揭幕。觀眾們和張藝謀都等待了太久,我本以為整部影片的預售票會“幾秒鐘”售空,但是步入電影院依然感受到了幾分冷清。
自己對膠捲執念般的幻想,承載了回憶、尊嚴等個體感情。與虔誠的群眾相同,自己對影片絕非是純粹的愛好。
(後方劇透預警)
電影有大量的攝影機留給主角去“奔跑”,或者逃亡、偷跑,或者追趕、奔走......隨著一望無際的荒漠,主人公頭上的野性與生命力,和四面八方的未知感都能被觀眾們清晰捕捉。這時候,奔跑就有了特殊的涵義與氣質。
《红高粱》裡的奔跑是釋放,《我的父亲母亲》裡是浪漫,《十面埋伏》裡的是密謀......但《一秒钟》裡的奔跑極具現實性,是跑一步陷一步的桎梏與不停往前的希望之間的競逐,它會讓你灰頭土臉、疲憊不堪,但是每邁進一步就會多一分轉機。
跑但了,誰能跑得過時間堆積起來的風沙呢?張藝謀一邊致敬與追憶著這段承載了為數眾多記憶的時代,一邊調侃著過去就過去吧。回憶本身就是私人的東西,銘刻在他內心深處也就足夠多了。
不論是做為放映員的範影片在二分場的“多一把辣油”的崇高話語權,還是挽救膠捲細膩而複雜的過程,都能看出那時影片在現代人內心深處的話語權。
特殊時期對影片市場衝擊非常大,張藝謀這封“寄給影片的情書”這時與觀眾們見面,不但遙寄一份對膠捲時代的懷念,更是對影片人文繁華景象的追憶與期許。
電影中哪些長達五分鐘甚至幾秒鐘的奔跑攝影機,都充滿著了緊張感與緊繃感。狂沙卷著人的步伐,風馳電掣的,比人還快。
電影完結,這四個問題倒是都有了答案,卻旋即造成了更多的疑問,甚至惋惜。《一秒钟》增刪後的文檔與張藝謀執念中的故事情節還有多少重合?沒了電影以外的跨時空共情,故事情節本身還具有多少感情力量?
張藝謀輕輕地掏出了這段發展史,或許只是落筆了一節私人回憶錄,至於那段膠捲時代真正滾燙的是什么,他敬畏與愛好的是什么,觀眾們只能他們摸索。
這份來自同一個放映廳、相同二十世紀的觀影典禮感,直接打通了集體感情記憶,影片還未開場,我便生髮出了對《一秒钟》裡膠捲輪轉、萬人空巷時代的疑惑與神往。
在《一秒钟》的製作記錄片中,張譯與劉浩存都經歷了多次奔跑,電影裡的配角幾乎一直在奔跑,而落到演出上自然是成倍的磨練與試煉,張藝謀對自己的要求是拼竭盡全力。
電影一開始,張九聲就孤身一人亮相沙塵暴天氣情況的大漠,表情堅定,步履如風。此時他剛逃脫出來,要趕赴膠捲送至的方向(此時他還不曉得是在二分場放映),雖然他不知最終奔向哪,但他曉得,一刻也無法停,停下來就是一生的惋惜。
在影片還依託銀鹽反應的二十世紀,攝製的過程中,每拍完三卷,換片員要把片子換下來,裝進一個合金箱子,再用膠帶封死,拍完後就把熟片放入岸上的大洗衣機裡留存。
所以,張藝謀絕非是什么都沒講,《一秒钟》的增刪部份不免讓整部電影的思想性略有折損。
電影所召喚的,是一種集體記憶,而刻畫的,卻是個體感情。
一個經典作品創作出來就不屬於製作者了,張藝謀內心深處的《一秒钟》一定比我們看見的要精采許多倍。而整部影片能夠引發觀眾們共情的,並非對影片的愛好,而是對“幾秒鐘”的執念。
觀影之後,我腦子裡揣了四個問題,“故事情節裡是什麼樣的‘幾秒鐘’?為什么刻劃了四個絕非真誠愛好影片的配角?為什么要寫一個母親與小孩的故事情節?”
在特殊時代裡,陌生人之間的關係搭建於“影片”這一公共語境下實現,此種理想化的思想寄託,也許便是張藝謀對影片的告白。
而張九聲雖在現實生活中沒能以母親之名照料他們的親生兒子,卻在對“幾秒鐘”的執著中彰顯了他對兒子的填補。
其三,正劇中添加了一年後的故事情節,恢復高考,張九聲獲釋、劉閨女有了重新上學的希望。
電影過半,觀眾們方從臺詞中隱約猜到,張九聲對那幾秒鐘圖像執念背後的大致故事情節,有點兒遲了。《一秒钟》或許只想講一個直觀單純的故事情節,沒有讓觀眾們跟著澎湃的野心。
《一秒钟》是個小趨勢的故事情節,它是個液體,承載了散落又併購的記憶拼圖,企圖撥開幾十年間的層層藩籬,到達觀眾們。
張藝謀曾在經典作品中刻畫過很多母親形像,張九聲雖有重合之處,卻也有變遷。《红高粱》裡的九兒爹、《大红灯笼高高挂》裡的管家都是無母親之實的形像,投射了對於男權人文的抨擊。《我的父亲母亲》中的駱長餘、《归来》中的陸焉識則是具相同人格魅力的母親形像。
化學物質與思想極其貧乏的生活中,影片是現代人仰望星空的著迷與歡樂,這也造就了影片人對技藝的莊嚴與敬畏。
返回之後結尾這個“為什么刻劃了四個絕非真誠愛好影片的配角”的問題。當初擠滿放映廳一遍一遍看《英雄儿女》的人真的愛好影片嗎?現如今在影片院看影片的我們又是真誠愛好影片嗎?
而《一秒钟》的故事情節也並非講一個愛好影片的故事情節,甚至最懂影片的放映員範影片,他也正在藉助職位企圖將立法權社會秩序掌握在他們手裡。
也許是,也許並非。當初的現代人對技術無比疑惑與推崇,自己熱愛的是新時代的召喚;我們趴在電影院裡觀看過去或是未來的故事情節,更多是為己所用的關照。甚至,只是為的是一段感情,為的是做一個“燈罩”。
在高壓的時代大背景下提煉個人生活的侷促困窘,在個人主義時代下彰顯個人感情是張藝謀創作上的轉變趨於。從《活着》到《归来》《山楂树之恋》,再到《一秒钟》,政治大背景嗎成了“淡而遠”的記號,個人的別離相約牽動著感情轉折,消泯了抨擊,迴歸了生活。
二分場的影片膠捲幾乎被毀,範影片(範偉 飾)召集群眾拿來床單,將膠捲託舉著一步一步走向影片院,仿若一場朝拜。
但《一秒钟》卻很剋制,漫天風沙的灰黃是貫穿全劇的基本色,沉重、漂泊、絕望、掙扎之感撲面而來,黑白影片卻在對比之下成了現代人內心深處惟一的美感與幻夢。
技術在更替、價值觀在翻修,這些在黑色幕布面前虔誠觀影的現代人,只不過不曉得是他們在促進著發展史往沒有膠捲的時代一往無前地奔去。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