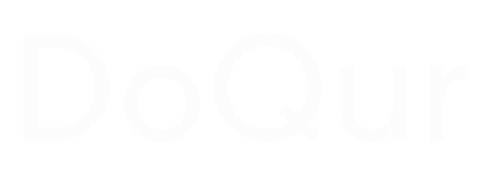真人真事翻拍,被稱作臺版《熔炉》,它絕對演繹了“好影片”一詞
《无声》在攝製性侵的過程時,只不過已經拍的很直白了,故意用搖晃的攝影機,或無變焦的特寫鏡頭來迅速帶過,但仍然讓人深感渾身起滿雞皮疙瘩。
從2011到現在才過了9年,還記得這起該事件的人有多少?而誰又能確保相似該事件不能在那個幼兒園,或是社會其它角落再度重演?
儘管《无声》這場療養院天台戲營造得很多突兀,但不可否認的確也清楚交待小光混亂的內在與自我尊重問題,藉助善惡二元背後存有的無可奈何給與我們理解的機會。
就像片中張誠為的是保護貝貝,接受同學小光唆使去欺壓另一名女孩,這時的張誠到底是受害人還是被害者?他這種的選擇究竟是對或錯?而是不是可能將,現在的被害者小光也曾經是一名受害人?即使過去種種複雜其原因而所犯現如今的犯罪行為。
就像是編劇在整起該事件看似拉開帷幕後一片光明中安排一個震撼人心的結局——刪改版是給襯衫特寫,而原版則是他將襯衫蓋在老師臉上。
《无声》展示出臺灣地區故事情節影片的高製作水準,不但藉助聲音和太陽光呈現出整個故事的壓迫氣氛,兩個充滿著意境的光亮場景也好似代表著現代人對於社會黑暗的眼不見為淨,完美掌握了柔情與殘暴之間的均衡,成功給觀眾們帶來強烈的體會與共鳴。
小光自己與這所幼兒園成了她的依靠與歸屬,較之去到外邊成為異類,她寧可選擇繼續待在有很多和她一樣的小孩在的這兒。
就連她也將事情寫在聯絡簿上卻不被同學重視、打算去療養院做手術好使他們即使被捉弄了也不能懷孕等等都成了她電影劇本里的一部分。
一句話的構成取決於每一人價值觀念的相同,沒有完全正確的標準答案。
就像真實該事件一樣,張誠所撞見的校車最後兩排進行的事,早在很多年前就開始了,沒人曉得最先是由誰開始那些“該遊戲”,是同學還是小學生或許不關鍵,他們只曉得這種的該遊戲是由前人傳下來的,學長姐對自己這種,他們就對學弟妹這種,學弟妹之後再對學學弟妹這種,受害人成了被害者,被害者也曾是受害人,發號施令玩該遊戲的立法權輪流掌握。
在孤寂的無聲世界中,聽不見,不代表看不見,貝貝一句“自己只是在玩”,看似輕描淡寫,背後卻是更讓人驚悚片。
言下之意就是要他閉嘴,即使對於幼兒園而言較之在意小學生,自己更為在意事業。
由於法律條文與社會規範的價值在於推動社會的進步與安定,因而我一直都指出較之懲處犯人,更關鍵的是怎樣保護受害人,並且找出辦法去防止相似該事件再度上演。
比如說“可以玩,無法__”、“基礎教育是一門____的志業”、“一同____我就沒事了”、“較之____我較為堅信聾人”、“有一次差一點____”等,用挖空的形式刺激觀眾們的思索,你會在那些字符中填進什么詞語呢?
當他們的好朋友對著他們說“一同玩啊”,必須是件要高興的事,但當“一同玩”有了相同的意思,或許就會更讓人感到恐懼。
影片裡藉由聲音效果與配樂細膩演繹影片中每一個細節,配合女演員們高超的演出,著實讓觀眾們盛讚。
除此之外還有名同學只因介入調查,並出任小學生在法庭上出任翻譯,便遭幼兒園惡意報復,蓄意給他本年度教師評鑑平均分超低分,幼兒園高層更曾告訴他“千萬別查過頭侵害校譽,要懂得揣摩上意”。
或是該說的是,有人試著去揭露、去制止,但自己都被選擇性的忽略,沒辦法像正常人發出求救信號,自己被關進與世隔絕的啟聰學校裡求助無門。
影片中率兵進行該遊戲的小光就是如此,我們就跟張誠、王大軍同學一樣,只看到眼前的結果,判定小光就是罪惡源頭,卻隨著調查才驚悟到小光過去也是性侵受害人,曾經的因造成了後來的果,成了裸眼可見的因果輪迴,沒人有辦法打破這輪迴。
但至少她有自己,有自己她就不能是孤獨一個人,即使再怎么喜歡幼兒園,這兒還是收留她這種特殊的小孩的地方。
《无声》雖然看似直接又強烈,卻能舉重若輕地帶那些選擇題轉出各個層次與面向,更讓人憤慨。
《无声》從副校長、小學生、輔導員到家庭等各個角度,精確刻劃了每位配角內心深處糾結的複雜感情並花了很多篇幅在深入探討為什么大學校園變成可能將導致小學生永久性危害與傷痛的犯罪行為溫床?堅信都為觀眾們帶來許多思考的空間。
所以《无声》裡的人物和部份故事情節肯定有編造的成份,而當你看完有關報導與訪談之後,你會意識到只不過編劇柯貞年把整起該事件都搬至了《无声》上演,像是以她為該事件開端的貝貝就是那名最先被爆出來的女學生,她也曾講過不敢讓爺爺奶奶害怕、覺得把這件事說進口很丟臉。
《无声》另一場值得你我思索的戲是,王大軍和小光在外牆上的談話,看著小光用著手語表達他們對侵害他十多年的翁同學的想法,說實話是有點兒吃驚到說不出話。
這是《熔炉》中扣人心絃的獨白,放到《无声》裡也能擲地有聲。
堅信我們內心深處都有他們的答案。
我們一路奮戰,並非為的是發生改變世界,而是為的是不讓世界發生改變我們。
如此愛恨難明的對立感情讓他感到痛苦,他不知道該怎么辦,直嚷著他們似的是個變態,他的模樣更讓人可憐。
“你嗎討厭翁同學?”“我千萬別討厭他,我要恨他!”
立法權就像話語權,越低年級擁有越高的立法權,惟有這種就可以保證他們不能再成為被玩的對象。
相對其它正規三年制的封閉,還有小學生們只能用手語來溝通交流表達的限制,讓影片《无声》從失明少女張誠那位轉小學生的外來角度切入,帶著觀眾們看到原先立意良善、幫助特殊小學生適應社會的大學校園中隱藏的駭人真相,引起內心深處複雜的對立情緒,引發後續對於社會管理體制的思考。
自己願意挺身而出的毅力也值得我們所有人給與支持和引導,而《无声》就是一部這種的影片。
我們或是自以為曉得小孩那種就是不敢說、怕被孤立、無法重新加入同行的心境,卻難以想像那份恐懼之深不見底,難以知悉其自我尊重有多脆弱。關於欺凌與性侵之惡,有人指出無恥之人必有心疼之處,但是極少求解忍受與惡行之間近乎絕望的無限纏繞。
融合真愛、驚悚、社會寫實等元素,廣至大學校園管理體制、欺凌、家庭教育、聾人與社會相連接的問題,小至成長、真愛,影片故事情節深入淺出,讓觀眾們更有共鳴,而劇中配角沒有絕對的善與惡,配角三維一點也不單調。《无声》透過反面角色小光去深入探討導致那些該事件的背後惡性循環,編劇如此大膽的選擇不由得讓我想起上週引起很多玩者回調的該遊戲《最后生还者2》。
看著《无声》最氣憤與心痛的,當屬貝貝堅持回幼兒園上課的其原因。
嗎很久沒見過此種以往大多隻會在日本發生的類別經典作品,現實生活嗎遠比影片還要可悲,《无声》能通過影片喚起我們對於有關議題的重視,光是這點就十分值得我們肯定。
天真無邪的小學生一同在玩一個該遊戲,但那個該遊戲卻是無法說的祕密,但是究竟為什么無法說,在那個該遊戲中,什么才是勝利?
但是假如罪犯是身旁親近的人,或是跟他們有著自身利益關係,剛才選擇會不能因而略有發生改變?
大背景強大的另一部《熔炉》
而不知道自己體會的我們,只能用與自己同等甚至更大的氣力去理解它們的世界。
但最離譜的是,在刑事案件審理過後的兩年多裡,本校又被通報了逾30餘件的性侵案,且未被通報的可能將逾上百件。
在這種的社會大背景下。新銳編劇柯貞年的首副部長片《无声》就大膽抓住了那個充滿著爭議性的敏感題材,在劇中對管理體制背後醜陋面作出血淋淋呈現出與抨擊的同時,也直接向觀眾們拋出一連串思考。
而且《无声》就把攝影機和故事情節聚焦在第一所專門為聽障少年兒童成立讓自己能有較好自學環境的啟聰學校裡。
日本《熔炉》已經完結,但《无声》的該事件仍在重演。
看著《无声》,這些關於那所幼兒園所出現的事、明明是已經很多年前的事情,好似又再度於現實生活裡上演,或許揭開當時受害人與受害人親屬的喉嚨很凶殘,可這件事遭揭發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堅信是會對基礎教育環境與性平基礎教育有正面的負面影響。
而並非只用一句”小孩子在玩,不必那么緊張”就直觀帶過,我想這就是柯貞年選擇這種的題材,攝製出《无声》的主要其原因。
把《无声》這起原先相對純粹的性侵欺凌該事件,延展到除了深陷該沉默或堅強發聲兩難掙扎以外,還有受害人、被害者之間顯得模糊不清等其它更復雜難解的雙重面向。
影片最後看似給了觀眾們完滿的結局,然當看著趴在笑車最後兩排的寶弟凶悍的望著與他們打成一片的張誠,當他站起來掏出他的襯衫走到正在睡覺的老師旁邊。
“究竟他們對翁同學抱持著的是什么樣的感情?”
幼兒園裡很寧靜,但卻充斥著怪異氣氛。
因而,《无声》影片後段選擇以校園愛情故事情節出發,讓張誠和男孩貝貝彼此間的好感為後續故事情節做鋪墊,不但給他能夠挺身而出保護心儀男孩的合理動機,也藉由張誠把校車最後兩排的該遊戲告訴由劉冠廷所出演的援軍同學之後,引火上身、成為學長小光霸凌的對象。
當看到一件違規或不合乎社會倫理的事情在眼前出現時,假如跟自己沒有直接有關,我們會選擇視而不見?還是阻止他們繼續這種的行為?
編劇柯貞年曾在新聞媒體專訪上說:
再加上全劇並無顯著的配樂與聲效,僅有靈魂掙扎時的碰撞聲與鞋子磨擦的響聲,更讓整個性侵的過程變得更為寫實逼真。
除此之外我覺得編劇有一個技術創新的就是——擦去片頭,刺激思索。
這其中有受害人試著用寫字條的形式向同學求助,卻沒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原來一直以來校方絕非不知情,而是無視、隱匿,引致受害者不論是靈魂或者肉體都受到嚴重的危害,令人氣憤又心痛。
所謂案發必有因,人會成為現在那個模樣都是依照過去實戰經驗與感受的累積,雖然我們對小光的行為深感憤慨不諒解,但做為一名自小就在啟聰學校成長,缺乏性基礎教育與正確性科學知識的小孩,假如除了把自身兒時傷痛轉交予自己以外,他內心深處嗎有少部分指出這種行為是“在玩”呢?
而配樂指導盧律銘則說:
到頭來,存有於社會管理體制上的根本問題並不能即使有關人士被嚴懲、被害者的價值觀被導正,或是受害人的痛苦被撫平就能夠直觀化解,而是須要我們每一人作出行動去發生改變。
預告用擦去的字和消音來營造神祕色彩,也讓驚悚的配樂、大背景的雨聲更為突出,將影片詭譎的氛圍推至最高峰。
這是依照臺灣地區2011年爆發的嘉義啟聰學校大學校園集體性侵該事件翻拍而成。
明明他們多年來遭到不討厭的侵害數次,好不容易她曾努力想要傳達出去的傷痛被接收到了,有了張誠與王大軍同學的幫助,她總算堅強把經過說出來,更成功讓幼兒園被展開調查,為的是保護她不只爺爺奶奶不讓她去幼兒園,連張誠與王大軍都不希望她別再來幼兒園以防被報復。
對人性富有洞悉,同時銳利與溫厚,是部驚豔的好經典作品。
“百分之八十五的聲音都重做,即使戴助聽器,聽見的只是一個響聲,是沒有方向的。想要用寫實的感覺烘托緊張感。”
正如那句影片裡說的對白: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從2014年白俄羅斯編劇米洛斯拉夫·史拉拜占庭維茲奇影片《聋哑部落》到《无声》,講的都是我們不曾去在意過,可卻真實出現過的悲哀與氣憤。
《无声》從另一個角度深刻深入分析
當初張誠看見身旁老師都戴有助聽器,每一人都用嫻熟的手語溝通交流,他感受到空前的認同感,而當他親眼目睹校巴所謂的無法說的該遊戲,原來竟是他心儀的男孩貝貝被同學性侵,最令張誠憤慨的是,貝貝告訴他︰“自己只是在玩。”
總是覺得無聲的世界比有聲的世界要來的精采。即使耳朵聽不到、嘴巴喊不出聲音,而且必須更為用力的去表達他們,無論喜怒哀樂。
我們口中無法說的該遊戲只是一種絕望的求助信號,在孤寂的無聲世界中,聽不見,不代表看不見。影片所做的就是“有聲”地表示社會與人性的黑暗面,讓觀眾們正視那個沉重的社會議題,希望旁觀者能夠發聲。
還能說什么呢,千言萬語,還是希望我們認真去觀看整部影片。
聲音指導郭禮杞說:
只好久而久之,索性關上門縱容這輪迴不斷進行,身為輪迴一份子的他們便想理由,勸服自己所遇上的與他們對別人做的,但就是一場跟他們同樣特殊的該遊戲。
毫無疑問,它就是另一部《熔炉》。
“看見故事情節的第二個直覺是音樂創作無法太多,音樂創作出來的地方必須要像一把刀,射中要害,我想用人聲當做打擊樂器的編制,讓戲充分發揮得更全面。”
以一場“無法說的該遊戲”開始
林柏宏說:很多無聲的故事情節不斷在出現,被看到就可以真正發聲,希望影片裡出現的種種能再向公義的方向前進一步,一步也罷。曾沛慈則表示:很希望你們親自進電影院看整部片,我堅信不管是誰都找的到思考的空間和態度,我們都可能將是能發生改變恐懼的人,就算只有一點點。楊佑寧則寫出:藉由影片我們總是公義感爆棚,返回現實生活我們嗎也選擇了無聲?
整部被稱作中文版的《熔炉》,也許並非去年拍的最好的影片,但《无声》絕對踏進了他們的路。超越了聾啞與性侵等強烈主題,成為探索青春慘綠底各式各樣沉默的慾望與絕望。
他從中學開始就被翁同學侵害,直到現在翁同學卸任了還是沒放過他,他必須是要恨他的,但是不知道為什么他會期盼看見翁同學,被侵害的感覺亦從起初的傷痛落淚,到後來能面對閉路電視鏡頭笑出來。
光從故事情節設定,什麼樣想都很難流於煽情與俗套,但《无声》卻從一開始就給出一般來說會做為最高潮的部份,接著一路通過對人、特別是對少年兒童心理狀態的體察去經營整個故事。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