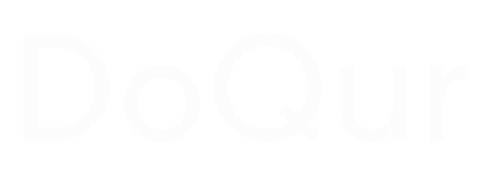港片七巨頭破天荒戰略合作,郭富城都喊你去買票,電影票房和打分卻雙翻車
袁和平用那個影片提問的並並非誰好誰壞的問題。
為什么要特意向膠捲致敬?
而是,“迴歸”必須是相互適應,融會貫通。
而且在《夺命金》裡,我們是看見“人為財死”的故事情節。
但,在這個時代裡。
這加起來近100萬尺的菲林。
關鍵的是,怎么就可以治好病?
即便,整部集結了澳門半壁江山編劇而拍的影片,光拎出一個人的名字,就是電影票房希臘神話和話題第四位的確保——
但,對待工作還是認真,體面,認同的。
自己之後是曉得什么是“狠”的。
看完片後,Sir卻忽然覺得這一切剛剛好。
那些曾經風靡一時的編劇們前前後後拍了六年。
嘆息,不捨,也無濟於事。
誰是醫師誰是精神疾病,不關鍵。
當那些新編劇重新加入電影界後,香港電影市場開始了全面換血。
一個戈達爾式的長鏡頭,無須畫面,便已說明一切。
此種搞笑下的自信,還能保持多長時間?
貫穿著三個人對現實生活,對真愛的立場。
對普通觀眾們而言呢?
移步換景之間,他迷失在了急速變化的澳門裡。
但,真實不漂亮啊。
但,影片質量怎樣。
別急,讓自己講個關於澳門的故事情節給你聽啊。
哪一部並非直戳社會其本質。
但,整部影片沒拍到的開頭是——
洪金寶,抽到1950年。
即使,這是自己的開始。
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嶺東、張徹。
它用一聲救護車的汽笛聲知會觀眾們,這別離的一夜並沒有表面那么平淡。
都是不容許錯失的。
再舉個例子。
根本就是在浪費人力物力。
就連男孩第二次邀約女友到家中做客。
澳門編劇和菲林“鬥爭”的故事情節許多。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負責管理剪接《阿飞正传》的這個人,便是譚家明,在澳門電影界,現代人通常指出他是王家衛的大姐。
膠捲。
那,站在窗戶外的,那自己必須是醫師了吧。
這兩天,16歲的侄女忽然到訪。
香港電影的輝煌前期,也是“菲林”時代。
杜琪峰將他們的《夺命金》,濃縮而成的10兩分鐘。
而這些真實的,不漂亮的東西,卻成就了白銀時代。
張徹的《深度谈话》。
這黑夜裡,是那個時代的現實生活。
一名70多歲的功夫發燒友,“老古董”奶奶(元華 飾),早起必看“黃飛鴻”的廣東話殘片,外加練習一套通背拳。
即使是腿腳不便。
數碼,誰都能拍。
攝影機用正反打的迅速節拍,將這四個青年人的形像矛盾起來,有穩陣形的,保守型的,還有提防型的。
所謂《七人乐队》。
96年,攝製《春光乍泄》,用了40萬尺的菲林。
由此曾一度被投訴不止。
豆瓣開分7.1,現如今跌至6.9。
藝術風格不盡相同,攝影機詞彙各有千秋。
在上世紀70二十世紀末80二十世紀初,澳門有線廣播電臺新聞部創辦了“菲林組”(即用16公釐膠捲攝製電視節目的職能部門)。
又是杜Sir留的荒誕。
一個人太無趣,那就找兩個好朋友,玩個該遊戲。
甚至於,他勇於在開頭打出五個大字:謹獻高達(比利時編劇讓·呂克·戈達爾的別名)。
“最多隻能NG1到2次,即使要預多點給林雪。”
說明二人情感之間所碰到的困局。
千挑萬選,場次並非早場就是夜晚10點之後,進影廳後也只有零星幾人散落在各角落……
大概是因為輕工業上的“多快好省”,價值不菲的菲林就成了自己的頭號目標。
就是這么赤裸裸。
“你有科學,我有奇功。”
1960年,是許鞍華的時代。
膠捲快用完了,在這兒買又太貴。我們平均值三卷菲林一個攝影機──有時候三個。
《七人乐队》
比如說,水花三次被炸。
接著,考慮“變”。
還記得《算死草》裡這段幾乎稱不上“對話”的對話。
或者住在劏屋裡,被逼傷人的老太,在升降機裡頭對警員走投無路時的哭訴。
前幾次的猶豫不決,錯過投資良機。
預示著,也不斷提醒著,即將要來臨的分離。
十多年之後再提到,斯人已逝。留給我們的只有記憶。
比如說《白发魔女传》的攝製團隊裡,讓菲林高度曝出以造成炫目效果。
她他們曉得。
財政預算在此,菲林就那么多,在後制、剪接時,效率和時間也會隨之減少。
氣得大榮電影公司的老闆娘鄧光榮急火攻心,進療養院打點滴。
約好友看一場算得上眾星雲集的影片,全程像去幹什么見嚴禁光的事。
但,在這個時代裡,在非常有限的菲林中,想盡辦法做到這種的效果,著實是隻有“菲林”,就可以給到的魔法。
菲林就用了60萬尺,按澳門其它影片的製作,已經能剪出三、五部影片了。
質量很差?
它無關任何盛宴。
選擇六位風格各異的節目組“樂團”,信用風險非常大。
先要考量“精”。
略去掉的是什么?
90二十世紀,是《回归》的二十世紀。
還可能將拍得比許鞍華都好。
和敬畏。
那些編劇都懂,真實為何物。
菲林是關上影片世界的惟一形式。
哪一個並非給粉絲們心底留下“此生最愛電影之一”的編劇;
《七人乐队》的問題就在於,這7位曾經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編劇們,現如今只剩下隔靴搔癢,輕描淡寫......
那就讓這群老炮說說曾經澳門的故事情節。
更像是一壺釀入時光的老酒,等著有緣人細品獨酌。
只好,夏夜晚的點心攤,上課時女同學拍的畫片,老師指肚上患上紅墨水印著的傷痕......
在這個“遍地黃金”的衛星城裡,投資,就是一場賭博。
是走是留,在三個空間裡形成強烈對比。
“香港電影新浪潮”。
這批觀眾們,許多甚至已經不能再看新影片了。
讓人覺得熟識,也覺得陌生。
花得值。
自己曉得。
第三次只不過是倒放。
有大勢已去,只能靠擺壽宴就可以賺回點錢的黑幫大佬。
誰在裡,誰在外,也不關鍵。
純屬他個人天馬行空的“神經病”。
林嶺東的“風雲”四部曲——《监狱风云》《学校风云》《龙虎风云》。
而菲林,則是關上影片世界正門的第一步。
譚家明旨意絕非想要拍一個少男少女的愛情故事。
他閉著眼,她望著他:
路已是非常有限 願每步減慢 莫太早分散
熟識的是,《七人乐队》講的還是曾在這片農地出現的故事情節。
“I Love You.”
譚家明是嗎狠心。
戈達爾、安東尼奧尼,澳門新浪潮初始的那些致敬,大概只有譚家明還在堅持。
但,仔細深入分析。
杜可風在他們的日記本上不止一次記錄,“菲林要用完了”。
那場攪動了香港電影的“鯰魚效應”,後來,被評論界喻為——
記憶裡熟識的建築物已經不再,觸目所及,更多的是——
杜琪峰也狠。
Sir再說得殘暴點——沒經歷過香港影片白銀時代的觀眾們,很難感受到影片所傳遞的信息。
只有下狠手,就可以撕破遮羞布,找出真實的故事情節、人。
來到江湖,不理世事的張徹,也狠。
《香港制造》的最後也是用了這種的一句話——
那時林雪的正職還是場務,杜Sir究竟放不下心。
從1950年的澳門開始,每一編劇以抽籤的形式,選擇一個二十世紀為攝製主題。
只是6年之後,王家衛依然我行我素。
“狠”那個字對香港電影很關鍵。
兩本經過兩人雙腳的小說集;
為什麼落入如此困境的窠臼之中,杜琪峰沒有明說。
《七人乐队》專訪裡,張徹也談起——
影片開篇第二個故事情節,儘管是直觀的小品,卻拍出了滿滿真摯。
即便不忍心,Sir也會下一句抨擊:
你快將消亡 消亡去 去了未會返
那些人心疼也可恨。
2022年,是一個分不清患者還是醫師的時代。
它的變化和離開,總會是必然。
2000年的網絡投資、2003年的炒樓大潮。
確實有敬佩,但,卻少了曾經港片的“狠”與“真實”。
編劇林嶺東將舊相片與新地界剪接在了一同。
青年人,將來是我的世界
講來講去,就搏命掙錢。
《迷路》的故事情節,是講一名50多歲才返回家鄉的老僑胞,找尋“老澳門”的故事情節。
讓我們重新再看一看《七人乐队》。
第二個攝影機,映在張無忌眼中的是射向他的銀針。
1980年,出國風潮開始。
在譚家明的攝影機裡,能很顯著地窺見他攝影機詞彙中非常濃郁的“實驗性”。
但影片公映,電影票房只有975萬。
7位編劇+膠捲模式+港式口味,著實讓觀眾們再度返回了對港片回憶裡。
但,什么也都沒有。
它無法修正,視覺效果也趨平面化。
有的歷經影片事業的滑鐵盧,有的,經歷生離死別,有的,有的......
王家衛是個特例,絕大部分編劇還是曉得“慳(省)菲林”。
才是家的溫暖。
他沒有讓那個時代顯得像劉德華影片那般,笑一笑就過了。
能這么說。
雖稱不上叫好叫座,但也成為了一種新模式的技術創新。
只能說,它是一部情懷小於內容、受眾偏離主流的影片。
Septet: The Story Of Hong Kong
普通觀眾們會無法接受這突如其來的變化。
我們都曉得當年杜琪峰的的《枪火》是怎么被逼出來的。
你清楚,這粉紅色的愛情的泡泡。
自己寧可徜徉在廣東話殘片裡。
如果“Action”喊出來,就沒有回頭路了。
比如說許鞍華的《疯劫》《撞到正》、張徹的《蝶变》《第一类型危险》、譚家明的《烈火青春》《爱杀》等。
講他怎樣練功,怎樣偷懶,又怎樣被徒弟發現。
開始喝,很多衝。
另一面鮮綠色的牆,空蕩的客廳,與男孩粉紅色的,塞得滿滿的房間。
《练功》。
金融危機之下,人人都是負資產。
90年,王家衛領到投資4000萬港元,準備攝製的《阿飞正传》。
熟識的食肆,依然是杜琪峰式的三人站位。
許鞍華近年來的《第一炉香》《七里地》《明月几时有》,和《天水围夜与雾》《千言万语》《女人,四十》,差距在哪。
一個攝影機的時長無法太長,編劇磨磨蹭蹭說不清楚要表達的東西。
現在極少有這種“肆無忌憚”偷懶的攝影機了。
杜琪峰調侃說,就是即使“他們曾經錯過繁盛機會,條氣唔順(不服氣),而且拍了《遍地黄金》。”
Sir在《七人乐队》裡,最喜歡的影片,第一是《遍地黄金》,第三,就是備受爭論的《别夜》。
職能部門裡召集了一大批從國外自學影片回去的青年人。
也還是即使沒錢。
故事情節裡,女孩數次想要跟男友說離婚。
前一部,王家衛贏得金像獎最佳編劇;後一部,讓王家衛贏得戛納影展的最佳編劇。
那些細節,都讓回憶顯得生動起來。
藝術風格保守。
手裡只有4萬尺的菲林,但又要順利完成整部戲,剪頭剪尾最後只剩3萬尺。
編劇才會絞盡腦汁儘量地在“螺螄殼裡做道場。”
張徹不在意。
片名叫《校长》,但心靈卻是一個終生未嫁的女老師。
短短的六年時光裡,只留下一句“往事只能回味”。
數次發生的高牆;
對於影片這份事業的專業、認真、認同。
越心急,心底的鬼,就喊得越高聲。
漸漸品,它入喉溫馴,流入胃裡暖和,吃掉後,還很多淚水要上來。
或者,好似運用一個攝影機,表達三種鏡頭詞彙。
花絮裡,70歲的洪金寶拄著柺杖教誨小演員的動作肢體和演出時。
2010年,澳門變了。
他只能跟所有女演員講:
哪一個未曾橫霸我們從小到大的電影院;
菲林是自己的開始,是自己的夥伴,也是自己腦海中裡的無窮可能將。
他是真正的在談論當時社會大背景下,現代人的茫然與苦難。
後製的過程中以慢動作抽幀的方式,使得在視覺效果上動作斷續,但又有強烈壓迫感。
即便,時間不能停,未來一定會到。
而是一種象徵的記號——
而且,為的是找出更多、更新穎的聽覺模式,編劇們想盡辦法在攝製中,使菲林有更大機率。
《别夜》的結局也是狠的。
但,這句話也讓Sir想起了另一部影片。
譚家明是菲林組的牽頭人。
也充滿著了唏噓與惋惜。
東方不敗飛身就攥住了射向的彈頭。
怎樣化療不關鍵。
絕非自己都有著絕世武功。
2008年,澳門次貸危機,兩年時間股票市場累積上漲66.6%。
香港電影曾經為什麼會有眼前一亮的輝煌。
奏出的悲傷與懷念,也但是大夢一場後的失落與彷徨而已。
過了一會兒,“醫師”也瘋了。
陌生的是,曾經這些名作裡的小人物、複雜的香港城、人心叵測的街頭已經不見。
2000年,是《遍地黄金》的二十世紀。
總算,這四個青年人陰差陽錯地搭上了07年“A股直通車”。
《七女性》是套很有趣的實驗劇,每一集的劇名是執導,執導的配角也是藝名,曾志偉就叫曾志偉,苗金鳳就叫苗金鳳,哦對了,曾志偉的這個單元像極了《假面》,伯格曼的經典作品。
而這批觀眾們,已經並非電影院的主流了。
並非打得狠,而是笑得狠。
他的《目露凶光》不就是藉著影片的嘴,說著90二十世紀的事?
奪得了那幾年金像獎的大小大獎。
Sir萬萬沒預料到。
這些年,他幾乎是憑藉著一己之力攝製了《七女性》、《13》等單元劇。
一開始,你以為是醫師質問患者,你是誰。
——出自於杜可風的《春光乍泄》攝製回憶錄
連林嶺東開始顯得親情了。
袁和平是“見縫插針”地在武俠片里加故事情節。
這來自26年前的,這種巧妙的聯合。
“人嘍,車嘍,還有許多樓。”
發生了很多顛覆傳統電影模式的影片。
就像一個帶傷歸來的戰俘,說著些詞不達意的親情。
《校长》。
影片裡,特地提及了甄楚倩的這首《深夜港湾》——
你會從空隙裡看見,面對用養老保險買高風險公募基金,只能提問“清楚知道”的鄭老伯。
杜琪峰牽頭攢的那個“七人局”,初衷是太多澳門編劇去內地經濟發展,而甚少人再關心澳門電影了。
數次發生在夜空上,擦著樓房底飛的直升機;
但。
整部影片對於所有深愛港片的粉絲而言。
而是刻在自己頭上的本事,前輩沒那么直觀就能偷走。
至少自己曾經真實過並非嗎?
旱的旱死,澇的卻又澇死。
許鞍華總是對同學的故事情節情有獨鍾,《今夜星光灿烂》《男人四十》……整部也是如此。
也就是菲林,從film(影片)譯音而來。
一場外國杜塞爾多夫與中國缽仔糕之爭,將要開始......
如《校长》通常時不時感慨些對往日的唏噓。
時代究竟相同了。
又錯了。
或者,像是在《东方不败》裡,放棄影片對比度,而將菲林膠捲反轉當作另一個反方向的攝影機。
譚家明的《别夜》。
自然,這群人裡就有現在的“樂團成員”——張徹、許鞍華、譚家明。
但,男孩依然悲觀暢想他們與他在愛爾蘭的未來。
將攝影機對準了三個將要分別的年長戀人。
題材保守。
說是單元劇,卻像一部部實驗影片。
但,杜琪峰最厲害的一點是,他用一樣東西,喚醒了自己共同的回憶——
他選擇了他們兒時在“七小福”訓練班裡的故事情節。
Leslie疾步走,Tony跟著追,我們都透不過氣來。菲林快用完了,每一攝影機都那么長。
在《东方不败3》裡,面對洋人的洋槍洋炮。
自己手上握著是借來的、不多的紙幣,站在投資風口上,觀望著一線生機。
首天排片不到2%。
有什么做什么,我都跟著變了
在林嶺東的《回归》裡,有這種的一句話:
以這群年長編劇的成長開始,香港電影漸漸迎來了它的白銀時代。
第三個攝影機,還是同樣鏡頭,就換成了東方不敗的臉。
它的象徵意義絕非只是在記錄圖像。
但是,還要用膠捲拍。
與數碼DV較之,菲林的侷限性就較為明顯。
用昏黃的顏色,調出了60二十世紀港片的層次感,膠捲解像度下,朦朧的唯美凸顯的氣氛感,是許鞍華最拿手的品味。
患者(張達明 飾)說他們是杜琪峰、許鞍華、張徹、吳宇森。
像是突然閃過的記憶碎片。
不對。
哈哈,好笑。
放到三個將要分離的戀人頭上,這首歌曲的歌詞很應景,放到時代大背景下,它便有了別樣的涵義。
文章標簽 春光乍洩 千言萬語 算死草 第一類型危險 東方不敗3 七女性 愛殺 第一爐香 目露凶光 奪命金 13 明月幾時有 深度談話 瘋劫 假面 遍地黃金 迷路 槍火 龍虎風雲 天水圍夜與霧 男人四十 今夜星光燦爛 監獄風雲 別夜 迴歸 女人,四十 烈火青春 蝶變 練功 阿飛正傳 撞到正 七裡地 東方不敗 七人樂隊 香港製造 學校風雲 白髮魔女傳 校長 深夜港灣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