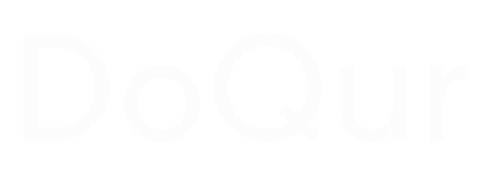張徹:希望能聚集澳門所有編劇再拍經典作品|訪談
《七人乐队》編劇群像版海報。
張徹:(我們)並非很難就可以聚在一同,我們一同見面的機會極少。像我比如說看見洪金寶、袁和平和譚家明的機會都極少。我和杜琪峰、林嶺東聚的機會是多些的,經常趴在一同吃個飯聊下天,大家相互取笑一下。那假如要聚集八個人去閒聊,我想只有在許多影展時能有可能,但現在影展又並非那么難舉行。你說用視頻(閒聊),那又並非很多人討厭用計算機,那也並非很多人討厭用智能手機。那假如說見面如果,有時候,我們看大家的公映的經典作品,就當做是一種見面。
【寄語】
拍完《七人乐队》,給張徹非常多感觸,他告訴南方週末本報記者,希望《七人乐队》之後,澳門所有的編劇都能聚到一同再拍一個經典作品,甚至再拍兩個經典作品也罷:“即使我們以前做過那個事,把所有編劇聚到一同,拍一個影片,那整部影片,無論拍得好不好,都是會令澳門編劇有更多增進親情和相互瞭解的機會。但是還會有一個很關鍵的象徵意義,就是我們那些編劇總算能一同做一件事情。”
張徹:玩遊戲和影片的方式有許多種相同,智能手機也罷,計算機也罷,電視機也罷,二維也罷,都有相同的效果。我堅信創作人一定會依照相同效果創作他們的經典作品,而且我不指出影片院會被智能手機替代。許多人用智能手機看影片為的是便利,影片院也有精采的地方,要做選擇的觀眾們是很清楚這一點的。害怕?是害怕不來,怎么害怕呢?比如說禽流感一來許多影片院都須要歇業,這輪不到我們害怕。人類文明的演化程度是我們難以發生改變的,我們只能應變,依照相同二十世紀的經濟發展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張徹主演了《七人乐队》中的《深度对话》。
至於攝製效率非常有限那個問題,幾乎《七人乐队》中每一編劇都有碰到,張徹也不例外,他想在一個非常有限的條件裡盡力去做許多能做的事情,他構想在劇中設置一個新房子,新房子講訴的是外邊的世界,那外邊的世界是什么樣的呢?那就交予觀眾們自行判斷。這段對話講了很多火星的問題,人生的問題,男女性別的問題,究竟是誰主控著誰?做為觀眾們和創作人的關係在哪裡?要讓張徹給那個影片做個總結:“只不過對話就蜻蜓點水的講了一下,沒什么深度的,《深度对话》就當做是他們給他們風趣一下吧。(笑)”
“沒深度”地深入探討了許多有深度的問題
南方週末:這一次《七人乐队》邀請了澳門最具代表性的六位編劇參予,我平常見面閒聊敘舊的機會多嗎?
張徹:製作每一部影片都很困難,每一部戲的困難也不一樣。比如拍《七人乐队》都是不容易的,為什么呢?最開始它叫《八部半》,做為8.5分之一,你要講什么呢?我時常被人問“你拍得順不順利?”拍完所以順利,但實際上拍的這時候會碰到相同的問題。比如說(要面臨)他們的健康問題,(面臨)有什么樣的創意設計問題,加上戲的難度、技術、財政預算等,都會碰到問題和困難,難到你很難去分輕重。這么十多年,拍每部戲都像在搏鬥,用盡他們的力量去搏鬥才會讓那個事情有結果。
採用膠捲攝製是《七人乐队》的一個明確規定,也是影片的一個民族特色。要問張徹用膠捲攝製有什么不一樣,他說沒什么相同,除了攝像機不一樣,其它都一樣。“膠捲只不過就是有看不出鏡頭的懸念,只不過攝製起來還是當年的感覺。只不過我還原的並非膠捲,而是還原膠捲的這個二十世紀。這個二十世紀的人拍影片時非常緊張,會緊張膠捲夠不夠啊?夠不夠時間拍?究竟是不是財政預算買膠捲?那種緊張感真的是很深刻。現在我們用數碼。只不過膠捲能做的東西和數碼能做的東西有非常大差別,膠捲後續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我們拍出來之後會想許多東西,就可以讓膠捲沖印出來的是我們想要的東西。但現在我們很難找地方沖印膠捲,無法看見他們拍的是什么,就給了大家非常大的期盼感,膠捲就是這樣。”在張徹心底,經歷了膠捲時代,看著後輩走回來,隨著同行走回來,再用到膠捲只不過內心深處會有一種神聖感:“做這件事,膠捲的確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工具,膠捲拍得不太好,許多這時候就是沒得補救的,我們要想辦法怎么拍得好才行,此種體驗是最珍貴的。”
張徹:我和杜琪峰、林嶺東都是廣播電臺出身,在廣播電臺工作時,我們常收工後見面、喝茶、閒聊,聊大家討厭的影片,聊看見哪個編劇的戲較好。我們四個人就想著一同拍許多我們討厭的影片,來紀念一下四個人的知己和兄妹情感,後來就想到比不上我們拍一個《铁三角》,但當時坐下來聊了好久都沒想出來究竟必須拍什么,那比不上我們每人拍一半,製備一部戲,這是一件高興的事。我們那么多人拍一部戲,能多接觸,多聊許多天,多一些瞭解大家那時候的想法。創作也罷,(經典作品有)個性也罷,想做什么都好,拍個影片我覺得挺值的,拍得好不好是除此之外一件事。
編輯 黃嘉齡
【訪談】
南方週末:你從業十多年,在影片行業裡碰到最難忘的挑戰是什么?
校對 陳荻雁
南方週末:我們現在基本在用數碼的方式觀看影視劇,比如說傳統電影院也受到了在線視頻的衝擊,你怎么看待此種“升級換代”?
影片《七人乐队》最後一個壓軸故事情節《深度对话》由張徹主演,暱稱“老怪”的他一直擅於在經典作品中玩“天馬行空”概念,此次他尤其設置了一個讓人遐想無窮的未來空間,用有意思的對話和驚訝的劇情反轉來敘述未來,以此來致敬澳門、致敬膠捲。做為澳門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從1979年主演電影成名作《蝶变》開始,張徹就一直在創作上不斷嘗試和技術創新,他主演的新派武俠小說電影曾將澳門電影的特效提高到一個新高度,但除了武俠小說驚悚片以外,他有時候也會用他們的形式來講訴不一樣的電影,比如說《深海寻人》和《女人不坏》等。談及此次攝製《深度对话》,他笑著說整部短片的代名詞就是高興,講親情也好,說二十世紀也罷,就是講訴關於“我們他們的東西”。同時他也希望未來能夠多有相似《七人乐队》這種的經典作品,“我希望澳門編劇能走到一同,拍一個同類型的東西。並非一次,也並非三次,我希望有很數次,可以繼續戰略合作,拍一部或是好數部經典作品來代表我們的二十世紀,告訴觀眾們,有那些人在這兒。”
張達明和張錦程在《深度对话》中分別出演醫師和患者。
在張徹主演的《七人乐队》壓軸故事情節《深度对话》中,素有“老怪”之稱的他繼續玩“天馬行空”概念,通過兩個人在一個臥室中的對話,“沒深度”地深入探討了許多火星、人生、創作和反饋創作等有深度的問題。
南方週末:你曾與杜琪峰、林嶺東戰略合作過電影《铁三角》,嗎即使此種戰略合作模式促成了日後的《七人乐队》?
南方週末本報記者 周慧曉婉
張徹編劇在《深度对话》攝製現場。
“要每一編劇選一個二十世紀攝製,說實話,我只不過不曉得拍什么,八個人拍八個故事情節,拍一個二十世紀,但我覺得去碰觸一個二十世紀如果,能講的內容是很寬泛的,即使要在八個相同的時間講訴七件有代表性的事情。只不過我覺得最好就沒二十世紀。”張徹想了想,笑著說:“只不過我沒抽到(二十世紀),他們說我抽到是‘未來’,未來是什么呢?要製成未來感覺的東西只不過許多,做為八個編劇之一你去拍一個故事情節,最重要是將你當時、當下的感覺拍出來,我當時覺得,《七人乐队》來自我拍《铁三角》時,三人(張徹、杜琪峰和林嶺東)戰略合作拍一部戲的想法,我就懷著當初那種想法去想。我發現許多問題都會牽扯到影片人為什么會拍影片?為什么我們那么多人會走到一同做這種的事?我想從創作人的角度看我們周圍環境,看我們自己是怎么樣的。而且就想到整部《深度对话》。”
【創作】
這么十多年,拍每部戲都像在搏鬥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