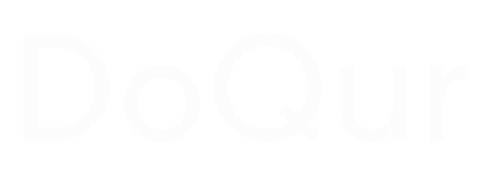本年度爭論鉅作來了!3年時間,阻斷女演員與外界取得聯繫,呈現出真實人性
該影片工程項目最初是為的是攝製一名前蘇聯數學家的傳記片(“DAU”是他名字後的四個拉丁字母),後延伸為持續五年的不間斷攝製,地點均坐落於國外北部小城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市郊。一個佔地約12000多平方米,對前蘇聯國家機密研究院進行原貌復刻的小型劇組。
現階段,互聯網上已經放出了《娜塔莎》(DAU. Natasha)和《退变》(DAU. Degeneratsia)三部。
包含醉酒“失態”與同事奧莉亞的玩耍、宣洩、到相愛,最後又返回意見分歧與爭執中。而她與生物學家盧克的床戲更是“真槍實彈”,風尚非常大。
影片長達137兩分鐘,比維也納影展的公映版本少了幾兩分鐘。全劇三分之一的片長都以“記錄片”式的表現手法、事無鉅細的表現了娜塔莎與他們的互動與溝通交流。
他還補充道:我敢肯定整部影片會在某國公映,即使它並非色情或暴力行為影片,那些元素也許存有但並非主要元素,它們只是人類文明脆弱故事情節的一部分。
1998年,一部《楚门的世界》在金·凱瑞的演藝下“封神”。整部影片用荒誕的形式,讓你先笑後哭,再絕望,鞭辟入裡地呈現出了“擬態空間”對於真實空間的蠶食與控制。
是什么發生改變了她?她變為了什么樣?娜塔莎夢想和期望的破滅,主體位置被立法權徹底架空,亦是電影的關鍵主題之一。大發展史對於小人物的發生改變,在記號性人物娜塔莎頭上獲得了表徵。
金·凱瑞出演的“普通人”楚門,自小開始就是生活在由影視製作托拉斯搭建的劇組中,那個高度“真實”的劇組裡,除了楚門之外,都是專業女演員。自己與楚門的交流被24半小時出鏡,外界的觀眾們盯著楚門與自己的一舉一動。
但電影最具爭論的還是來自片頭幾十分鐘的審判場景。男性對於娜塔莎的嚴刑拷問、思想羞辱更讓人背脊發寒。主觀性攝影機脅迫大眾直視了那場審判,直接展現了男性粗暴地對女性扒鞋子、扇耳光等一連串侮辱性的動作,甚至讓娜塔莎將一個空瓶子插入他們的皮膚部位。
電影以男主角娜塔莎為敘事主線,講訴了她與鄰近兩位關鍵人物的生活化日常。
這段一氣呵成,駭人且貼切的章節,令部份觀眾們深感嚴重生理不適,倍受煎熬、如坐鍼氈。據悉當時有觀眾們直接離場,批評編劇的動機。
系列影片《DAU》工程項目的誕生如驚天“核爆炸”,從它設立工程項目以來就受到大量的關注。
立法權的壓抑,催生了一個看似平淡、卻暗流湧動的行為閉環。娜塔莎看似“沒變”,只不過和發生改變,電影以她對同事的“最後一次警告”戛然而止。
被選上的400多人完全依照當時蘇俄的情景和生活形式來生活工作,但是完全阻斷了自己與外界的取得聯繫,所有與這個時代無關的東西全都成了違禁品。
劇組中,400名核心值班人員在五年時間裡,積極開展此項無影片劇本的影片創作,“真實再現”前蘇聯管理體制下的“生活形式”、人性傷痕,突顯有形的控制,壓抑的社會。
但,全劇最為精華的部份在於審判後,娜塔莎與審判女子的“相愛”,和電影結尾,她與同事奧莉亞即使完全相同的事兒再度陷於感情糾葛。
她與年長的女同事奧莉亞的兩場“醉酒”對手戲、她與數學家盧克的一夜灑脫、她最後遭受來自安全理事會(K GB)女子的審判,這讓做為咖啡店服務生的她,經歷了生活上意想不到的劇變。
接下來的一場戲,娜塔莎獨自一人在咖啡店的傷痛流涕,自言自語,亦是她心理上的徹底“企穩”。之後,審判來臨,管理體制對於她皮膚和信念的炸燬接踵而來。
浩瀚的素材最終被製作成14部影片長片。主題涵蓋社會意識、立法權爭權、人類文明感情,暴力行為操控等,都藉由圖像散播在聽覺復刻的描寫中。
整個影片工程項目的初衷是希望女演員和觀眾們都能以沉浸式的體驗,感知這段發展史下社會的各個方面。以此,更加精確和全面的瞭解和認知“大發展史、小人物”的主客體關係。
十多年之後,國外編劇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正式宣佈打造出小型的“楚門的世界”。為的是“真實的”重現一個時代,他把一大群女演員置放到驚喜搭建的小型劇組裡,給與女演員最大程度的充分發揮空間,他僅僅充當記錄者,用攝影機“重現”這群女演員“返回過去”時的真實狀態。
而堅持觀看完全片的部份觀眾們從電影表現手法上也給出了評價相對較低的判斷,指出影片故事情節沒有大背景交待,語義脫落,故事情節本身感覺就像是一個粗略的,很多雜亂無章的片段拼湊。
毫無疑問,《DAU》是影壇的歷史性該事件,它就像一顆投入池水中的石頭,註定要颳起非常大的浪花,讓平淡的水面盪漾不斷,在不斷蔓延向邊緣的漣漪中,我們或許能看見藏於水底很久的種種未知。
直至有一天,楚門洞察了其中的擬態真實。但他並沒有拆穿一切,而是反轉了“看與被看”的主體位置,開始操控起一切,憑藉著他對片場和劇組的熟識,以唱功矇騙大眾,成為了真正的“主導者”。由此,“被看”不等於“被控制”,主動的看或許反倒成為了被操控的一方。
《楚门的世界》已經在網絡時代,大大擴張了他們的疆域,真實和虛構的界線不斷被打破。有時候虛構的比現實生活的還要真實。
對於這種一個恢弘而史無前例的影片工程項目,任何個人體驗都侷限於觀看者本身的既有認知體系,旁人終究無法全面感受,這也註定了其非常大的爭議性。
娜塔莎始終希望從無趣、乏味,無望的生活中脫離出來,酒精是她壓抑生活的惟一進口。當她碰到生物學家後,以為一夜的溫存能激活生活的死水一灘,但最終卻只是激情而非真愛。
但胖哥卻指出,電影的主線敘事仍然沒有徹底擺脫章節化或段落化的敘事內部結構。從電影開始、大力推進,到完結,娜塔莎與奧莉亞前後三到三次的“交手”,人物心理微妙的弧光轉折,就是電影主題的空隙處。仔細對比兩人數次對話中的行為和語態發生改變,就能發現其中的暗喻。
三部影片也在維也納影展上首映禮,最終《娜塔莎》在影展中斬獲優秀表演藝術重大貢獻銀熊(攝影)獎。不得不說,《娜塔莎》(DAU. Natasha)絕對是一部反常規類別,對於大眾粉絲的審美觀偏好頗有挑戰的“實驗性”電影。
影片公映後,爭論不斷,某國更是以影片風尚問題頻繁上綱上線。對此,編劇伊利亞還是為他們的經典作品作出了辯解:在《DAU》系列電影中,探討的是關於人性的話題,不給人機會去看它是很可笑的事情。
3年時間裡,那個現實生活版的“楚門的世界”的工程項目總共積累了長達700個半小時的35公釐膠捲素材,前後少於1萬多名臨時演員,參予復刻出1938至1968年間,第一所坐落於聖彼得堡的前蘇聯研究院的當時狀態。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