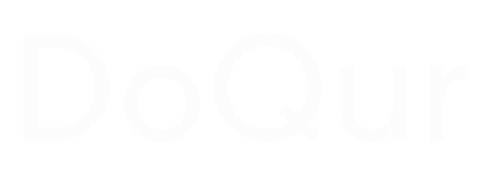華語電影史最大惋惜,他沒改編成張愛玲
總有人說,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不太好改編。
以信的內容推斷,起因該是王家衛想拍《半生缘》,給張愛玲寄了他們經典作品的錄像帶。
為拍好《海上花》,侯孝賢請作家阿城出任藝術指導,任他牽著整個片場,蘇州北京地跑,翻淘古時古董傢俱。
參照該文及書刊:
曾經也想改編前作的編劇田壯壯,覺得呈現出它的最好方式是電視劇。
先後兩部影片《倾城之恋》《半生缘》《第一炉香》,和一部音樂劇《金锁记》。
要再挑戰直接改編張愛玲,堅信執著的侯導,可能將真會上天入地去找尋各式各樣“黴綠斑斕的銅香爐”。
[4]《恋恋风尘:侯孝贤谈电影》
假如侯導足夠多膽大,他也許才是拍《第一炉香》的第二編劇。
張愛玲沒來得及看,但後來考據出,她另寫信問過宋淇妻子,可否聽過王家衛編劇的姓名。
在王家衛認為,他的《半生缘》已經有了。
這梳子往上一梳,嚇走了蝨子,也刷糙了袍子,自然沒了個香味。
巧合之下,發現信的歷史學者又和一名老編劇,聊起這事,才弄知道前後緣由。
以致於開頭那句經典的“世鈞,我們回不去了”,也品不出幾分世隨時移的蒼涼。
而在一眾華語片大導演中,對著張愛玲傳世之作搓手欲試的,又不在少數。
內容如下:
他先是想拍《红玫瑰与白玫瑰》,男主角訂下林青霞。
那許鞍華直接大喇的個性,平實樸實的圖像藝術風格,就像一把“日常實用卻色澤粗硬的梳子”。
區別於李安版,楊德昌更想拍這個二十世紀大北京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並且做了很多殺青前的案頭工作。
單以《花样年华》的兩張片花,張迷就能腦補出《倾城之恋》裡淺水灣賓館附近的那堵牆。
一在選角上摔跟頭,二抓不許動畫版的氣氛意蘊。
範柳原曾對白流蘇說,這牆讓他想起了天荒地老。
許鞍華的《倾城之恋》固然失利,倒也促成一陣陣翻拍張愛玲短篇小說的影片熱。
即使《半生缘》藝術風格大改,張愛玲文字裡的“玄妙”,人性裡的幽深,依然重要,她只看見故事情節中便於截取的配角和情節。
女主角王佳芝,依然屬意林青霞,男主角易先生,則邀請民國初年爆紅的北京女演員雷震。
許鞍華按他們的理解,刪繁就簡地拍完,影片前半段故事情節倉皇急促,有如走過場。
他聽了直接說對不起,我拍不出。
可“難”也是嗎。
似乎他會是她的知音。
當年,只不過是那位老編劇託王家衛給張愛玲寫信。
坊間曾一度廣為流傳著,一封信張愛玲給王家衛的回信。
許鞍華討厭卻不懂張愛玲。
看似一場天作之合,惋惜了之。
從最先的《倾城之恋》,到現如今被吐槽成《第一炉钢》的《第一炉香》,許鞍華改編張愛玲,說來說去,總存有三點問題:
即便兩位主人公的感情變化和經歷,太過複雜和坎坷,難拍出狗血奇情。
自小愛讀劉氏短篇小說的許鞍華,是個不折不扣的張迷,最初也只心心念念改編《半生缘》。
給的理由,也挺有說服力,“這個繞來繞去,這個幽微,對我來說太難了。但是一定是講北京話,一定是北京這個二十世紀的氣氛,這是很很難的。”
終是修復出短篇小說裡,老北京素樸灰疏的生活況味。
《倾城之恋》當年既不暢銷也不叫好,粉絲尚能接受的《半生缘》被林奕華直指“羞辱”動畫版,《第一炉香》還沒公映,已經不受待見。
編劇許鞍華就一次次用他們稍顯“失利”的經歷證明,的確如此。
撿回兩條“命”的楊導,沒拍成電影整部《暗杀》,則一起身拍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誰才是改編張愛玲的最佳人選?今天想來,聊出答案。
所以侯孝賢想都不敢想,要費上非常大氣力,但是“光找女演員就找死了。”
在翻拍張愛玲短篇小說的各版背後故事情節中,欽佩許鞍華的毅力,也遺憾王家衛的沒能成行。
張愛玲或許成了許鞍華編劇職業生涯裡,一處始終翻過但的山地。
楊德昌:越想拍,越惋惜
[3]《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
但又覺得拍沒法,有難度。
而也有說法,王家衛的影片,分明是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變體。
還說只有電視節目人,敢大膽拍張愛玲,同時也把張愛玲拍壞了。
只是,張愛玲想在大熒幕上“回魂”,更何況仍要再等一等。
她在《许鞍华说许鞍华》中寫,《半生缘》是最適宜他們拿來拍的。
她宣稱張愛玲太難拍,他們完全理解不對白流蘇和範柳原的心理動機,最後《倾城之恋》出街,變為“堅強而大膽的失利”。
這恰是她拍不太好的證明。
只為復刻她筆下帶出的這些生活傷痕。
王家衛呢,受訪時稱過他們也很討厭《半生缘》,要拍出張愛玲短篇小說的思想個性,只能多拍“神”,千萬別拍“形”。
侯孝賢站王家衛的理由,很直觀:
郭富城參演風流倜儻的浪子範柳原,張曼玉不必換下蘇麗珍的禮服,學著低頭,也能自帶白流蘇嬌滴滴的韻味。
歷史學者馮睎幹寫他倆,“七分貼切,二分煽情,兩分睿智,永遠計算精密,保證你即便故事情節人物都忘光後,至少還能打包一大批金句。”
兩方約好臺灣地區相遇,結果曼玉這邊又想調整下檔期,惹得暴脾氣的楊德昌不甚愉快,直接則表示不用我愛你。
“《东邪西毒》就是武俠小說版《半生缘》,《花样年华》就是王家衛版《半生缘》。”
聰明的編劇,常常選擇三流的短篇小說去翻拍,即使空間大、自由度高。
王家衛和張愛玲,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故事情節。
結果籌備良久,片方又要等因《红高粱》名聲大噪的鞏俐,參演另一名男主角。
假如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就像她那句“華美的袍子,下面爬滿了蝨子”。
只是,張愛玲在寫完一封信的三個月後,便撒手過世,想必最終也沒有寄送。
許鞍華成為翻拍張愛玲經典作品最少的編劇。
[2]《许鞍华说许鞍华》
“即使它較為樸實,不必靠許多很玄妙的聽覺或是鏡頭來表現效果,而是在人物關係上彰顯,我想會較為難拍。”
老編劇是王家衛的徒弟,去年已有72歲的譚家明,被告足等了大半輩子,才等來回音。
劇名改成一看就會暢銷的《暗杀》,體量甚至比李安拍的《色,戒》還大。
再努力的許鞍華,也許也註定拍不太好張愛玲。
她沒把他們變為一個張生物學家,反倒有時候言論像個“張黑”,比如說她評《倾城之恋》,就是“一個衛星城沉沒,成全兩對狗男女”。
林青霞不願繼續等下去,最後只能作罷。
侯孝賢:張愛玲都被拍壞了
在澳門的一次專題講座上,侯孝賢曝料徐楓曾經找他拍《第一炉香》。
“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什么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或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假如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邂逅了……流蘇,或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誠,或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誠。”
全劇又以39個長鏡頭,大規模地遊走在長三別墅那個脂粉樓內,生怕露了不對味的馬腳。
許鞍華:翻拍最多,失利最多
在他內心深處,只有一名編劇有能力拍好。
王家衛:《花样年华》就是我的《半生缘》
其中,就有一名日後成名的大導演,彼時拍片沒多久的楊德昌。
《色戒》薄薄數十頁的短篇,等到李安拿來翻拍的這時候,也把人煎熬夠嗆,拍完直接大病一場。
後來拍完他們的正式成名作《恐怖份子》,楊德昌又開始著手準備張愛玲的《色戒》。
那人,是王家衛。
開頭不太好拍,直接放棄,上片頭
不光經典作品裡的對白,猶如師出同門,能作感情互通。
很難講,一切嗎影片之神的暗地操縱,《牯岭街》才是最適宜楊德昌的表達。
家衛先生:很開心您對《半生缘》拍戲有興趣。久病一直接到信就只拆看賬單與極少數急件,而且您的信也跟其它好友的信一同未啟封收了起來。又因對一切電腦都奇笨,不能操作放映器,接到錄影帶,誤認為是熱心的聽眾寄到我共欣賞的,也只得收了起來,等之後遇上有機會再看。以致於躭擱了那些時都未作覆,真的抱歉到極點。病中難以觀賞您的經典作品,非常惋惜。現在重託了皇冠代斟酌作決定,請逕與皇冠洽談,免再延擱。前信乞約略再寫一份給我作參照。匆此即頌,大安。張愛玲八月三日,一九九五
許鞍華改編張愛玲,在攝影機詞彙上更顯蒼白,不夠美,也不夠精巧。
他和李安,無意去還原張愛玲的文字,只是想借下殼子,去拍許多別的東西。
據傳,也找過張曼玉。
至於好不容易拍上的《半生缘》,選角難得沒出錯,卻終究無形無神。
他長在北京又遷去澳門的出生大背景,讓他有能力呈現出張愛玲短篇小說裡的那種“北京風華”。
文章標簽 紅高粱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色戒 半生緣 再見楊德昌:臺灣電影人訪談紀事 紅玫瑰與白玫瑰 戀戀風塵:侯孝賢談電影 暗殺 東邪西毒 牯嶺街 金鎖記 第一爐鋼 第一爐香 色,戒 海上花 花樣年華 許鞍華說許鞍華 恐怖份子 傾城之戀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