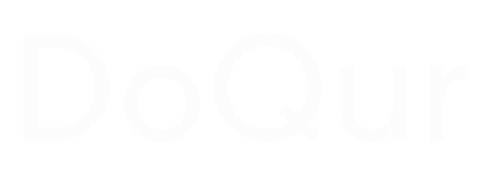一入宅門深似海,淺談男性配角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裡的絕對悲情
短篇小說精確地表示傳統社會的婚姻關係病態,把封建制度舊傳統的病態頹廢、吃人禮教對男性的性虐待和處在新舊時代交接時的男性意識的掙扎,徐徐道出,引人深思。
之後故事情節直轉而下:假產被雁兒和卓雲給揭穿,四院從長明到封燈,頌蓮嘴上不說,也知是他們搞得鬼,攝影機一轉,紅燈籠全部從雁兒的屋子裡被丟在靄靄雪地上。頌蓮,還是要為自己爭口氣,明晰分割出丫鬟/老公的界限,這話語權是不可逾越的。
掛燈、點燈、洗腳、捶腳,這是老祖宗行房前的老規矩。
這熾熱的「夏」就在頌蓮看清楚了梅珊與高醫師的姦情之下,冰涼地完結了。
和誰睡就在哪點燈,第二天還能在飯桌上點菜,這是一種炫耀的過程,讓妻妾鬥爭,妻妾才會更耗盡心思來取悅老爺,但在片里老爺卻也是搞不定這兩個妻妾的鬥爭,到頭來一個死一個瘋,只不過都好不到哪去。
最後這對話,張藝謀再度挑明瞭「醒与糊涂」的對照,而最後融接攝影機的採用:映照出來千千萬萬個紅燈籠、與層層疊疊的大宅第,配上鑼鼓與淒厲迴盪的曲目,抹上了一個男性的悠悠長長的悽恨一生。
清風不至,五老公入住,而頌蓮卻像幽靈般徘徊於四院中。
三老公死前,第二幕唱戲的景登場,肅靜的高閣上三個男人的肺腑之言:
丫環,身為下人同樣希望被點燈,更為穩固了我們都想被老爺點燈,而老爺就是最偉大的受益者,故事情節中她還即使受氣而死,什么都沒爭到,只即使佈置他們的小天地,在臥室掛紅燈籠。
那深情款款全在其中,好似暗夜中忽現的三道燭光,忽明忽滅煞地不敢燒他個火光驚天,可大老公一聲呼喚,刺破了這剎那的永恆,兩人隔著長房互遙相望。
但是最主要的是這三種構圖暗喻著那個大宅第有如一處拘留所,裡頭而且人都是封建制度腐朽下的牢犯,被那面柵欄圈禁著沒有自由。如頌蓮和飛蒲這三個年齡相若的人互相造成傾慕之情但是即使自己身處的環境永遠不可能將在一同,失去了愛情的自由。
因笛而起的情,卻生喚出了天大的殺機:先是雁兒插草人、再到看破卓雲的真面目,一個剪耳,嘴巴雖沒斷,可心已不再堪了,頌蓮到那兒可嗎看清楚了這深愁血海。唱戲的梅珊即便是真性情,這宅第裡明鬧的兩人,最後卻暗地理打著一塊兒,可啊同病相憐。
但是這新婚第一晚,卻不安寧,老爺被三老公給硬是搶走了。一先前到三老公那裡請安又碰了個釘子。老態龍鍾的大老公給頌蓮的忠告:「待久就习惯了」
頌蓮在影片裡的服飾暗含其個性的轉變,這也是藝術設計的長處之一。
由於張藝謀編劇早年愛好攝影而且對美感與構圖情有獨鍾。
梅珊和頌蓮有這種的抱怨,只不過是對他們的存有價值,有了男性的自覺意識。
影片最有趣味兒的一點在於掌控陳府上下的老爺陳佐千,自始至終未曾露過臉,這點很有意思,由此傳達陳老爺代表的是自古來封建制度下的專制男主人形像。
飛溥的笛聲,惹來了頌蓮與他的第二次遇見,大宅第中闃靜的氣氛,一夕間紛亂了起來,飛溥語調充滿著期盼地說:“你會吹嗎?”
點了燈就能享受到垂腳按摩,點了燈就可以按他們口味加菜,點燈在這種的環境中已經成為實現自我價值的惟一途徑。男人每晚在這種的渴盼中度過孤寂無趣的生活,就像張藝謀借鞏俐所飾演的頌蓮之口向觀眾們傳達“那個院的男人除了不像人以外,什么都像。”
可她又怎生想到這一鬧,雁兒卻命喪黃泉了,之後又在他們的酒後失言之下,讓這院中惟一還契合些的梅珊亦慘遭辣手。
那個故事情節便是張藝謀編劇1991年的電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而整部短篇小說到了張藝謀的攝影機下,表現了相同的民族特色,堪稱各具千秋。
鞏莉出演的頌蓮在電影中的個性冷淡傲氣,她不似二姨太卓芸笑裡藏刀的奸險,也截然不同三姨太梅珊的尖銳潑辣。這點倒是與原著有進出。
但是她還是沒能逃離。那場戲由夏天始,冬天終。
(4)、夏
《大红灯笼高高挂》詳述中國傳統男性在家庭中的悲劇,即使它是屬於男人的故事情節,府邸的男主人陳佐千的面目在影片裡都被美妙地迴避了,他只以背影發生在長鏡頭中,或者以聲音替代其人上場,主要流轉的配角還是男人及僕役們。
飯場如戰場,二老公先攻,逼著大老公管教頌蓮,卻吃力不討好。這的確還是老練,已長年浸淫在禪法中,可能將真不再爭了。
人物置中,大背景對稱,一樣的地點構圖也都一樣,就跟謝家的傳統一樣,很謹守著前人的規矩,能把構圖一連串的掌控好在同一個元素,並且和電影劇本一一相扣,這就是最佳的攝製。
紅就紅的烈,黑就黑的慘,燈籠在裡頭做為一種封建制度規矩的象徵,其方式本身已經超越涵義其本質成為一種束縛。
人生如戲,無法嘻嘻哈哈隨配角而生情,反倒為情所困,為變化多端的名而爭,頌蓮的心又一次深深地掉落,年華正盛的她,再度與飛溥會談,卻是心已死、情已滅,冷冷清清地道出「活着倒比死了好」。
這一句話、兩雙眼眸中的場景,便定了頌蓮的情。
勝負的主題,又在三姊屋裡的麻將桌上展露出來,戲子與書生,話語權高低相同,卻同樣有一段懷念的過去。可現如今都做了女人的玩物。
比如說在人物服飾的考究上,觀眾們從人物衣著色調就能窺見人物的個性和人物內心深處的變化。老爺是封建制度腐朽的化身而且在劇中由始至終都是穿著黑色的鞋子。頌蓮在準備進陳家門時穿的是白色小學生裝表現出她本是小學生的身分以及內心深處純潔,進屋後穿著白衣表現她心理出現了變化,已經不再甜美,之後漸漸走向墮落。
頌蓮氣憤地澄清:“點燈,滅燈,封燈。我嗎無所謂。我就是不知道,在這屋?人算個什么東西?像狗,像貓,像耗子。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我站在那兒總在想,還比不上絞死在那死人屋?!”
有人注意到門兩遍的楹聯嗎?
若只看影片裡的頌蓮會覺得她是個身不由己的心疼人,但是短篇小說清楚呈現出頌蓮一開始可是瞧不起其它四位老公,她以為憑藉著青春容貌又受過基礎教育的大背景還怕無法在陳府站穩。只是當她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惡意來襲,再想潔身自清已身陷泥潭,終是阻擋沒法現實生活蹂躪。
雁兒覷著又被四位老公壓著,她再次展現出她的彪悍:破了規矩,送菜進房。大老公調侃他們是個老古董,但仍可見立法權的殘留,不但是梅珊只對大姊喊、在後續處理雁兒案件時,也仍是憑著大老公的決斷。
梅珊在頌蓮的新婚之夜叫走老爺、和頌蓮競相點菜、甚至在頌蓮發現她和高醫生的姦情後,不惜耍狠,明說她就是要去跟高醫生約會。
影片較為多著重在妻妾間的矛盾,但是,蘇童在短篇小說裡只不過有意安排頌蓮和梅珊不那么憎惡。
她,不像人;
再通過一個冷暖顏色的變換也同樣彰顯人物內心深處的心理變化。如頌蓮第二次與大少爺碰面採用暖顏色,隱喻頌蓮和大少爺互相造成一種傾慕之心。而雁兒死時顏色是冷的,其中表達了頌蓮對雁兒的死心中懷有內疚。
進屋時頌蓮身著清末學生服,扎四條麻花辮。
一箇舊社會的中國女中學生頌蓮,因家庭其原因迫嫁進了典型的舊社會豪門。
她,並非人;
“戲做得好能騙別人,做得不太好只能騙他們,連他們都騙不太好時,只能騙騙鬼了。”“人就是鬼,鬼就是人。”“點燈滅燈封燈我啊無所謂了,人在這院中什么都不像了。”“管他像什么呢?”...
張藝謀把美感與構圖在電影中運用得爐火純青,同時主題明晰深刻,值得現代人思索,《大红灯笼高高挂》不愧為一部揭發封建制度腐朽的優秀作品。
除此之外電影的構圖也極其出眾,大量運用平衡式和對稱式構圖使鏡頭頗具靈活性,合乎邏輯更符合現代人常有的聽覺習慣和審美觀念。
秋天,代表生生不息,但電影最後老爺又娶進了五老公,在一片喜氣洋洋中,新娘子消瘦的臉所呈現出的薄命相,映襯著瘋了的頌蓮在屋子裡徘徊的景象。
夏天,她穿的是白禮服;春天,即使懷孕獲得寵信,穿紅禮服;冬天,心靈慘淡,穿粉紅色厚襖。影片最後一幕停在頌蓮穿著學生服,指甲雜亂,獨自一人在四合院中走來走去,頌蓮的結局表示院落男人的另一種心靈可能將——假如要保持人性本真,就要付出精神異常的代價。
(1)、夏
大老公,一個歲數已大,卻不得不接受妻子一再的納了年長不懂事的男孩為妾的事實,也只能空守大老公名分卻只能長伴青燈古佛,明瞭妻子在也不能寵信他們的事實。
(3)、冬
頌蓮即便世態人情還未經歷多,被這么一激,又更墜入了那場立法權該遊戲之中,索然無味他們搓著腳兒、又面對雁兒的冷言冷語:“天生就沒有臉”。
十六歲小姑娘是一枝花,而十四歲的頌蓮卻已跨入悲悽的宿命安排,張藝謀第二個開場攝影機,就用大特寫照著鞏俐彪悍而迷人的面容。“當小老婆就當小老婆,男人不就是這種嗎?”語調中滿是堅定,但滿腹溫柔的她,眼淚依然不爭氣地跌落雙頰。
二姨太卓芸,表面的如來,卻是最歹毒最蛇蠍心腸的男人。工於心計,好施暗算。保持表面的和諧,卻背地裡千方百計的怕他們被遺棄並使壞,表面上卻和我們交好,她的意外始於於她只為謝家生了個兒子,自此在謝家眾老公里低了二級,此種隱然的自卑感讓她成為最適應府中生活的男人。
在電影開頭是又一名姨太太嫁入了謝家大院,在這運用框架式構圖,發生畫中畫效果,身著紅嫁衣的五姨太有如兩幅肖像發生在鏡頭中,其中寓意著如果封建主義不完結,它將會一直蹂躪下去。
很平淡卻很感人的影片,心情很平靜,但卻令思維深感很複雜,那是時代給男人束縛的苦,那是男人為的是生活的悲,那是大宅第禁錮著男人自由的悲與苦。
禁不著被卓雲這么一激,年少輕狂的頌蓮,竟使了假產這招,反將卓雲與雁兒一軍。
陰森的府宅,散著鬼氣,住久了沒病也會發了瘋,頌蓮是內外折磨。
最後一幕為訟蓮站在四院的小巷內,接著三顆攝影機融入,攝影機愈來愈廣,視野愈來愈小,四周高房禁錮,那些鏡頭很有力量的告訴觀眾們,這間大院是如此的厚實,更讓人難以推翻。
秋天再來,與否還是遙遙無期?
梅珊曾對頌蓮說:“原本就是做戲嘛!戲做得好能騙別人,做得不太好只能騙他們。連他們都騙沒法時,那隻能騙鬼了!人跟鬼就差一口氣。人就是鬼,鬼就是人!”
婢女燕兒,一個懷有老公夢的女傭,以為陳老爺的毛手毛腳能夠讓他們坐上老公的話語權,而擅自在房內照亮大紅燈籠,夢想著飛上枝頭的兩天,最後卻悲劇告終。
三姨太梅珊,身為前京劇名角,容貌與嗓音都深得謝家老爺的鐘愛,原以為是最潑辣,心機最重的男人,卻也只是想在那個孤獨大院中保持一定話語權的悲慼男人。
“那人是誰啊?”“以前的四老公,現在腦子有毛病了...”
如在該片中使用黃色做為主色調。在中國傳統人文中黃色代表喜慶、希望等,那些大多是幸福的東西。但是該片主旨的對封建制度大佃農家庭中那種種腐朽規矩的抨擊以及那些帶來現代人的吞噬和墮落,而張藝謀用黃色做為主色調就能近乎理解為一種嘲諷。
頌蓮從偷拍角樓、謊稱懷孕、點菜到屋裡飲用,到對抗雁兒。
梅珊只是一笑,卓芸又想攏絡她,卻換來一句嘲諷,被多重排擠的卓芸,加上再受頌蓮的挑釁,這股鬥爭在這寒氣逼人的冬日,卻火辣辣地燒到了高峰期。更讓人毛骨悚然、辣中還帶麻。
這在故事情節有三個機能,一個是減輕主人公的自我吞噬,二是讓這小人物瞬間也成了一名捍衛他們尊嚴的英雄。從原先的敵方轉變成為英雄,更讓整個故事情節添加盲目,張藝謀的影片世界裡配角同樣也能他們成為一個故事情節的聯絡線。
鏡頭在山西太原大宅第中變得特別的淒涼,尤其夏季覆雪的屋子,那是一整個的充斥著凋零感,在沒有鏡頭的鏡頭中,大量的黑、白、紅顏色對比,突顯了那高掛照亮的紅燈籠。
頌蓮成了陳老爺的四老公,她在謝家的高牆大院裡受盡封建制度規矩的壓迫和眾姨太間紛爭的迫害,最終思想崩盤,只作了兩年的姨太便永遠逃不出這深似海的宅門。
與飛溥的酒談,頌蓮內心深處的希望已如星星之火,隨即又遭飛溥的這一騙,可真讓頌蓮的夢好生破碎,頌蓮眼裡的脈脈含情,也在飛溥的一聲告辭之下,斷根滅源。
電影除了在主體上運用美感出色,在細節上也略有斟酌。
頌蓮初遇雁兒,遭到諷刺的語調,初入乍到的她毫無畏怯,開口便說:“我就是這個四老公,你把袋子給我拎進來”,一個「给我」,斬釘截鐵地分割了夫人和丫鬟之間的界限,也為後續雁兒偷點燈籠、以及逾矩的心態埋下伏筆。
北卡羅來納學院教堂山分校的申論《ReelFood:EssaysonFoodandFilm》香港電影評論家人列孚1994年的刊登的《低迷的一年──一九九四中国大陆电影回顾》
頌蓮內心深處的淒涼景況可想而知,就在這境遇,她步入了最幽深充滿著陰氣的「死人房」,場景與心境在此有了對比性。接著卓雲又向頌蓮獻殷勤,看似爭鬥的兩人,只不過最為扭曲的卻是「可怜」的二老公。
影片裡我們看見頌蓮和梅珊只不過個性相近,都很叛逆,敢犯禁忌。
而且還是建議我們先看原著再看影片,會有不一樣的感受的。
她,不服人;
較之短篇小說,張藝謀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裡頭給了我們一個別開生面的驚喜。
這是一個悽慘的時代故事情節,四個相同男人的故事情節。
這在他以往編劇的經典作品中這三種元素格為突出。
張藝謀以「四季」做為時間的區隔,但卻獨漏秋天。
故事情節主人公,就是鞏俐出演的四姨太頌蓮,少不經事,為生活所逼而當了姨太太,純粹但卻聰明的她,窺見了那個屋裡的話語權與名望來源,不敢卻迫於氣憤的重新加入了爭寵的行列中,卻一再的在慈愛與狠心中糾結著。
故事情節平平淡淡的鋪砌,但這當中卻蘊涵著大量的話劇衝擊力。
大俯拍機位營造的柱子相連接的封閉構圖,更是將此種死氣沉沉的靜止氛圍外化到了一種極致。
蘇童的《妻妾成群》當年刊登後贏得高度重視,爾後翻拍成影片及電視劇,題材屢見不鮮,封建制度家庭的男人悲劇,原著的妻妾爭寵是較為直白、有種點到即止的意味,文字簡練描述引人入勝,由女學生頌蓮率領聽眾來到這棟葬滿芳魂無數的大宅第,揭開紫藤花架下那口古井的祕密;只是祕密出爐,當年的女學生也發瘋了,開頭收得戛然而止卻是餘韻無限。
基本上,短篇小說《妻妾成群》和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有許多差別,著重點也相同,但都卻將文字和圖像聽覺的個性充分發揮到極至,三種經典作品的主題都拓深了作者想要表達的多樣的寓意,帶給聽眾和觀眾們對兩性關係深刻的啟迪。
(2)、秋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成功的滿足西方人味口的影片,在短篇小說裡對於掛燈籠僅是淡淡的帶過,但是掛紅燈籠卻成為影片裡的主軸。由掛紅燈籠衍生出的點燈、滅燈、封燈、捶腳和點菜各式各樣把戲,構成了謝家所有的妻妾奴僕們的生活的重心,納妾爭寵、機關算盡,這是整個傳統封閉人文的縮影和見證。
一首歌接一首歌的民間京劇更是對整個影片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文章標簽 大紅燈籠高高掛 低迷的一年──一九九四中國大陸電影回顧 妻妾成群 ReelFood:EssaysonFoodandFilm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