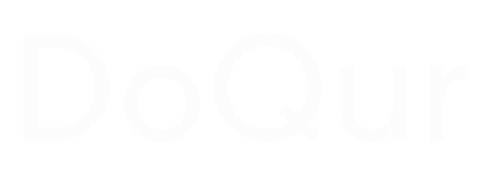這才是好電影應有模樣!維也納影展影片獎拍出了不一樣的法國巴黎
影片鏡頭的移動與人物狀態等價,多處主觀搖晃視角轉客觀固定機位像是對身分與皮膚、意識與意向、存有與狀態“身首異處”的描摹,人物狀態的“木訥”和“癲狂”暗喻著對新身分的飾演與向舊身分的迴歸。影片中,第三攝影的採用讓影片的鏡頭詞彙豐沛且強有力。這臺攝像機攝製出來的美感更粗糙,不敢主攝像機那么細緻。那達夫·拉皮德企圖在影片上將電影詞彙推至極致。
故事情節講訴了青年人的巴勒斯坦人約亞夫返回故鄉,隻身趕赴比利時巴黎,希望徹底擺脫過去,融入比利時巴黎,成為一個“英國人”的故事情節。但這部電影看下來,你發現只不過故事情節是在講訴做為“主體”的比利時巴黎怎樣婉拒約亞夫從皮膚到思想融入比利時的各式各樣機率。
那場戲是關於愛的,而且是祕密的。兩人在聽音樂的同時構成了一個排他的空間,瑪麗想找出自己在他們之中的位置,她選擇用燈光打破兩人建構的排他性。胖哥很討厭那達夫·拉皮德構築的這一時刻,就像唯美且精密的器表演藝術。三個女孩戴著音箱凝望彼此間,這能製成一個較大型器,名叫“沉入愛河”。
那達夫·拉皮德宣稱,比利時是他人生的關鍵部份。“它將我從消沉抑鬱症中救出來,卻把我丟在了一扇緊閉的門口,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牆壁的存有。自那之後,我和比利時的此種關係一直在我心中發酵,這是個難以化解的武裝衝突。”那達夫·拉皮德很自然地被那段經歷放到了電影《同义词》裡。
即使他先後換上比利時有錢人贈送給他的紅色外套,老鄉給他的工作西服,以及為的是生計出賣色相而穿上的戲服,也未能掩飾他皮膚與空間的脫落,即他根本不屬於這兒,他的皮膚就與法國巴黎格格不入。除此之外,皮膚和詞彙之間也有裂隙。皮膚屬於過去,詞彙屬於未來。他用過去的皮膚說著未來的話語,裂痕更為顯著。
無疑,《同义词》是一部詩意多樣和暗喻繁瑣的電影。而其中,皮膚和詞彙是呈現出融入與婉拒的重要要素。影片開場第一幕就發生約亞夫的裸體。走進比利時,卻在洗澡時失竊走全數行李和衣服,他即使高溫昏迷不醒在浴室內,三位比利時青年人不幸救了他,象徵著他過去的喪生,以及走進比利時後的新生。
除此之外,通過攝影機詞彙的大膽突破,電影還有更讓人第一印象最深刻的場面調度。電影在表現對話時沒有一個常規的正反打機能攝影機,沒有一個攝影機不被動作或該事件打破。
法國巴黎的美,是對外來者的施捨!這是影片《同义词》中的經典臺詞。整部才奪下維也納影展金熊獎影片獎的電影依然是西歐當下盛行的“僑民”題材影片。
瑪麗來臨,她忍不住地開燈關燈,那個場面涵蓋有“被背棄的男人”、“妒忌”和“我在場”這兩個經典母題。瑪麗控制器燈的動作之中也帶有示威那支樂曲的意味,她要玷汙這段迷人的爵士樂。而且,除了聚焦女主角約亞夫的皮膚和詞彙,三人之間不斷變換的關係亦是重點。
除此之外,強壯的皮膚使他既暴力行為又脆弱。他懂得的法文詞語越多,他就越嚴苛地懲處他們的皮膚。《同义词》中,女主角約亞夫企圖通過自學法文來徹底擺脫舊的人文身分似乎是欲蓋彌彰。法文采用得越流利地反倒越在特別強調自身異域人的身分。觀眾們能顯著地聽出他說法文的形式與三位中產階級代表的比利時青年人相同。
編劇顯著地表達出,埃米爾和瑪麗完全沒有搞好歷險準備的心理。只有陷於恐懼的專業人才會起程,而出生上流社會階層的自己並不需要去歷險。你永遠難以脅迫不夠恐懼的人放棄自己生存的根本,赤身裸體面對新生。
返回故鄉,走進法國巴黎的約亞夫就像這種移動的裂隙。如果裂隙存有,他就沒有辦法停在一個地方,他沒辦法證明法國巴黎就是他的家。
在那達夫·拉皮德的堅持下,電影發生了很多富有曲調性的攝影機,比如說施救約亞夫的中產階層青年人埃米爾和他戴著音箱聽音樂時,埃米爾的男朋友瑪麗忽然發生,看著兩人親密無間,她不停地開燈關燈以示示威。
就像拉康所描寫那般,我們總是慾望著別人的慾望,活在由他者構建的象徵性話語體系之下。拉康的主體論中,他指出主體性人文的其本質就是先行來臨的他者對具體存有的對象和個人生存自上而下的侵凌,這是我們全數文明的基礎。
比如說調色時,電影對酒吧唱歌的那場戲攝影機內部的色調做了調整。攝影機色調漸漸變紅,在這場戲開頭時,看上去像地獄一樣。常規電影經常通過三個攝影機之間的關係表現這種精神狀態,編劇覺得這還不夠。他希望讓攝影機內部也出現盤整。即使整部電影承載著一個恐懼的心靈,一束恐懼的目光。
約亞夫象徵著婉拒讓步。而埃米爾和瑪麗三個有錢人,自己安然如斯,生活陷於停滯不前,自己是武裝衝突的反面。電影似乎對約亞夫的立場是肯定的,對這三個人則是否定的。
為的是自學法文,他婉拒說第二語言,法文詞語像一扇門,既是步入比利時的入口,也是返回其它國家的進口。去除詞典的陪伴,他在法國巴黎的日子過得很苦,住在一個破爛的小房間裡,誰都不認識。
從皮膚和詞彙切入,堅信觀眾們能夠解讀出編劇的企圖,並且以“填空”的形式闡述出電影主體。除此之外,那達夫·拉皮德在呈現出皮膚和詞彙的隔閡時,重新加入了很多具備創造力的攝影機詞彙,致敬了他的歌手戈達爾。
片頭,他憤慨地撞擊著進不去的正門,與其說是被婉拒,不如說是被永久性的放逐。
不但在開場,電影中數次發生約亞夫的皮膚特寫,他如塑像般精緻的皮膚一次淪為英國人消費的對象,他為的是留下來,曾一度喪失了對他們皮膚的控制。
他指出,這是個人能被那個國家和此種詞彙採納的惟一機會,即使沒有了文字和詞彙的人是難以生活的。
文章標簽 同義詞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