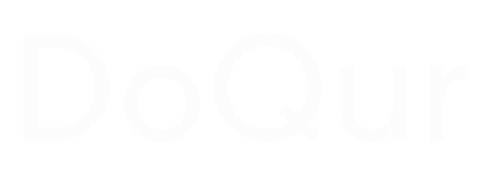大師丨斯皮爾伯格:怎么講一個“成功”的故事情節?
老斯:是Sid Sheinberg找出的這故事情節。他對我說:“我覺得你必須把那個故事情節拍出來。”只好他就把那個故事情節賣掉了。但是在那時候,實話說我覺得還駕馭沒法猶太人大屠殺此種題材,而且我那時候還有許多片能拍,能很多已經做了準備了。我之後拍了《夺宝奇兵2》,再拍《辛德勒》,跨越太大,太難了。我覺得自己還不夠成熟,無論是自己的拍戲的水準,還是對於表現大屠殺的情緒上的準備。只好我就一直想把那個片推給別人拍,但是他們都又推回給我。
本報記者:荷里活有個說法是“別在河裡攝製“。約翰·羅賓斯有一次告訴我說,拍《圣保罗炮艇》的這時候他都快被逼瘋了。
老斯:我曉得《慕尼黑》是我政治性最強大的影片。我們在拍的這時候,我和Tony Kushner有這時候會趴在一同探討現代人會怎樣理解整部影片。他甚至說:“整部影片會引發許多噪音,這肯定不能是壞事的。”我就說:“假如會有什么壞事呢?”他說:“這可能將要等到10年之後才會有吧。現在一公映如果,肯定並非這種的。”
本報記者:影片確實有種白色影片的層次感。
老斯:我一直想拍《世界之战》,結果艾默裡奇的《独立日》發生了,有點兒把我的計劃打亂了,我得重新找個講火星人侵略地球的故事情節的角度,那就是,千萬別火星人。我們想到的是一個對他小孩不怎么好的媽媽,為的是挽救保護自己的小孩,在這兩天裡成為的是最偉大的媽媽。我覺得影片超額完成了那個效果。
老斯:我起初的想法是想把它拍成影片黑白。這天我在給Whoopi Goldberg視鏡。我是和Gordon Willis一同給她視鏡的,Gordon Willis是個好攝影師。我當時就想用黑白拍,即使只不過我對他們並不怎么自信。我怕他們把那個故事情節毀了,怕他們把它講訴得過於花哨。但是假如我用黑白拍如果,那就不能變得花哨了。可能將吧,我第二次退縮竟然是為的是不敢把影片拍得太漂亮。後來攝影師改成了Allen Davieu,他和我還是決定把影片拍的漂亮點,無論是面部還是內外景都要漂亮。我覺得觀眾們或許會記住影片的迷人,以此蓋過原著那種暴力行為的意境。
老斯:我一直以來都想拍一部戰爭片,接著我有了拍自然主義戰爭片的機會,而並非虛假的戰爭片。事實上,我還剋制了想要把它荷里活化的衝動。抨擊的現代人是即使影片裡有個紐約市來的也有個猶太人,只好自己就會說:“噢,你用的是Lewis Milestone在《白画进攻》(A Walk in the Sun,1945)裡用過的梗。你拿族群和人文的組合來顯示美國人是從世界各地來的。”這一點都不困擾我,即使自己看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片根本我沒我多。那些抨擊也不能對於《拯救大兵瑞恩》導致什么負面影響。
老斯:嗎,我並非太清楚我在拍《横》的這時候對此有什么想法。我是依照報刊上的某首詩寫下的這個故事情節。報刊上是說有對情侶要把自己的baby從孤兒院接回來怎么怎么地。後來就被我經濟發展成了那個瘋狂的故事情節了。懷爾德的《倒扣的王牌》一直是我的最愛之一。這片子嗎負面影響我許多,比如說裡頭悲劇情勢下那種狂歡的氣氛和對資本化和奴役的表現。
老斯:《大白鲨》的成功得歸功於許多東西。其中一個是我有了最終剪接權。我有了創作的自由,而且是一直的。但是拍《大白鲨》對我而言卻是一個可悲的經歷。其原因之一是,電影劇本一直沒有順利完成的,我們只能邊拍邊寫。
老斯:John Williams對於我的影片是重大貢獻最少的。我所有的影片他只有一部沒有幫我作詞。他的重大貢獻是無法量化的,即使音樂創作在你神經系統作出反應之後就已經觸動了你的內心深處。在《E.T.》的開頭,ILM和我作出了腳踏車飛上天的效果,但只不過真正能讓人感覺飄在空中的是John Williams,即使他的大提琴配樂真的讓人飄飄欲仙。觀眾們隨著管絃樂跨過了星星,伴著自己降落的也是John Williams的音樂創作。我覺得《E.T》的最後15兩分鐘更像是芭蕾舞劇,這要歸功於John Williams。不止那些,我之後的影片,也都要非常感謝他
諮詢報名:
本報記者:你還在整部黑白影片裡把襯衫處理成黃色。關於那個,你是怎么考慮的呢?
本報記者:短短的一年後你拍了首部影片,《决斗》(Duel)。鑑於你那時候的年齡,拍的可算是很老練啦。你當時是怎么獲得那個拍戲的機會的呢?
翻譯:林詩釗
本報記者:你最近的影片都變得較為高傲,你覺得之後還會這種嗎?
本報記者:我曉得你本想把它拍成影片黑白影片的?
本報記者:《侏》是部CGI影片。你當時有意識到CGI應用領域裡的鉅變嗎?
本報記者:《大白鲨》和《第三类接触》都是商業上很成功的影片,在自己之後,你拍了《1941》,在這之間是出現了什么事嗎?
老斯:我一開始對於開場要怎么拍並沒有什么想法。我拍戲都是已連續著拍的,當然拍開場的戲也是已連續著拍的。開場拍的是登陸奧馬哈沙灘。拍那場戲的這時候,過程是很意識流的。我沒有用故事情節板,也沒有在計算機上畫原畫,所有事情都是這兒順利完成的(指了指他的屁股)。所有我讀過的關於在諾曼第登陸倖存下來的故事情節,近距離親身經歷的那種,此時都充分發揮了促進作用。我當時沒有預料到26兩分鐘的開場就要我們拍4周就可以順利完成。每次片場人員回來問我:“下週一我們必須就能拍完了吧?”我總是說:“我不曉得。“便是即使攝製是即興的,而且我覺得,假如影片裡有給你那種第三人稱的衝擊感,撲到你臉上的衝擊感如果,我覺得那是即使我當時也不曉得接下來會出現什么,就像一場真正的遭遇戰。
本報記者:很多對於《拯救大兵瑞恩》的評價是“過分荷里活化“了,對此你是怎么看的?
本報記者:一部分你影片的氣質來自於John Williams的配樂。你能說說那個嗎?
本報記者:那那個電影劇本也很巧妙嘛。
本報記者:你當時緊張嗎?你做了哪些準備呢?
老斯:我想必須是在我看麥克·克萊頓的短篇小說的這時候,我才決定要拍的。我當時還想到了《决斗》。嗎,我一直以來都想拍一部與爬行動物相關的影片,我是雷·哈里貝格的歌迷。
書名地址:http://www.dga.org/Craft/DGAQ/All-Articles/0604-Winter2006-07/DGA-Interview-Steven-Spielberg.aspx
本報記者:我們而言說《拯救大兵瑞恩》,雖然是個悲劇故事情節,但是沒有《辛德勒的名单》那么壓抑。整部片的計劃是怎么到你手上的?
老斯:CGI第二次用到商業影片裡,是在我製片人Barry Levinson編劇的《少年福尔摩斯》裡。ILM(輕工業光魔,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製造出了彩色窗上的騎士忽然變為嗎,接著跳出窗戶的效果。這甚至是第一個數碼特技第二次在商業上的運用吧。當然,第三個用的較為好就是克雷格的《深渊》(The Abyss)了,裡頭用了許多極致的數字特技。但是,用數字爬行動物來做影片主人公,那個事情還沒人做過。而且,能這么說,《侏罗纪公园》是第一步把成敗賭在數字特技好壞的影片。
拍戲之路怎么開始的:
本報記者:你曾經說過,假如沒有拍《紫色》的實戰經驗如果,你永遠拍不出《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你具體是什么意思呢?
老斯:我在電話號碼上探討過兩個半小時。有一次我們講了8個半小時,中間即使要吃午飯還停了一下。在80二十世紀的這時候,庫布里克說過:“必須你來拍整部片,而並非我,這更必須是你更會表達的感情,我不擅於。”他講過幾十次。庫布里克惟一一次積極主動地讓我參予的影片就是《A.I.》了。第二次他說:“我想讓你讀讀我寫的大綱。”在這之後,我們認識也算挺久的了,他也沒給我寄過什么大綱,《全金属外壳也》沒有,其它的影片也沒有。
本報記者:整部影片現代人談論的最少的畫面是辛德勒往下看一看到穿白衣的小男孩的那個攝影機。這個場景是虛構的嗎?
老斯:縱觀我所有的影片,《紫色》是我的成熟之作。這是我的第一步非爆米花影片。觀眾們須要自行藉助自己的實戰經驗和認知來理解那些配角。故事情節是從配角的對白中表現的,而並非那種鱷魚突襲旅遊勝地或是車追車的大場面。我心底清楚,雖然故事情節出現在迷人的鄉下,就像詹姆斯·雷諾影片的那種模樣,我想要表現出配角間的絕望,想要在田園牧歌的鏡頭裡講訴一個更讓人心痛的故事情節。
老斯:在拍整部影片的是,我想到了三個編劇。我覺得整部片是對科波拉的致敬,也是對皮埃爾·塔蒂的致敬。他在《于洛先生的假期》和《我的舅舅》的演出,表現了他的智慧,他擅於用他周圍的東西來使觀眾們發笑。
本報記者:你有預料整部影片會引發這種的爭議嗎?
老斯:那場大屠殺曉得的人並不多,只在許多圈子裡祕密地廣為流傳著。但是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肯定曉得。什么東西都無法減慢納粹黨對西歐猶太人的打掃的步伐。同盟國什么也沒做,除了一直在打戰。這就是為什么我要讓這個攝影機變為彩色的,就像小男孩頭上的襯衫那么顯著。
老斯:我未曾覺得《慕尼黑》和我其它的影片有什么相同。我更想把它看作一個必須被曉得的故事情節,而那這時候我覺得是這時候拍它了。它滿足了我的市場需求,去深入探討嚴肅外交事務的市場需求。我支持巴勒斯坦,我想通過此種真摯的非暴力的形式來支持這個地區的和平。
本報記者;沒有人攔下你嗎?
本報記者:影片一開始就是諾曼第登陸的日子。你預先是怎么計劃這部影片的呢?
他一個極佳的專訪對象。他聰明,有意思,有時候還有點兒謙遜——所以,他還是為他們的影片深感自豪,不論是這些晚期的娛樂片,還是中後期這些能引人深思的影片。
老斯:我並沒有有意地計劃什么。我並不會即使為的是讓觀眾們放鬆放鬆就得去拍一部爆米花影片。只要我覺得這時候到了,什么樣的影片我都會去拍。假如拍《林肯》的時機成熟了,我就會去拍《林肯》。對於《夺宝奇兵4》也是一樣,這時候到了我就會去拍。我是說,假如拍某部影片的這時候到了,我是可以感覺出來的。我也曉得什么這時候還無法拍。但是假如讓我跟自己戰略合作製片人如果,或是是去指導編劇如果,我還是會去的,比如說《艺妓回忆录》。那些都是依照直覺的,我75%的直覺是恰當的。我還是會聽從我的直覺。
本報記者:有人說你的編劇職業生涯是在為環球拍戲的這時候開始的,這是對的嗎?
本報記者:《大白鲨》在你的職業生涯是個里程碑式啊,但是似的有很多困難。對於攝製的那幾天你有什么好的回憶嗎?
老斯:並非的,是確有其事的。某天早上,辛德勒和他的男朋友在弗羅茨瓦夫猶太人區親眼看見的。他當時正在騎馬。他聽見一片喧鬧。各式各樣的運輸工具在猶太人區穿梭。我們在和辛德勒同樣的視角拍了那場戲,而且觀眾們看見的是和56年前的辛德勒看見的是一樣的。
老斯:是啊,每個人都叫我千萬別在河裡拍。嗎是,每一個人。Sid Sheinberg甚至說,“為什么不建個水箱呢?我們會給你錢的。”但是我說,不必了,我想到海里去拍,去認真試一試,我要現代人覺得這是嗎,鱷魚嗎在海里頭。我不敢讓整部片顯得像《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58)那般的影片,大背景一看就是畫的。我不敢要這種的。
本報記者:我們而言說你最近的三部電影吧。《世界之战》已經說過了,你還有什么想補充的嗎?
老斯:我當時想到的是Fred Zinneman的《豺狼的日子》(Day of the Jackal,1973),和Costa-Gavras的《独家新闻》(Z,1969)和Pontecorvo的《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1966)。我在處理驚悚片部份的這時候,那些影片一直在我腦子裡頭。
本報記者:你從小學到了什么嗎?
亞洲地區微電影聯合會衛星城菁英俱樂部—成員招募 拍微電影聯合亞洲地區微電影聯合會開設微電影編劇專業進修班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我專訪過19個英國編劇,從希區柯克到馬丁斯科塞斯。那些專訪對我而言都是很愉快的經歷,但沒有一次能比得上我最近這一次專訪斯皮爾伯格。以下內容就是本次專訪的摘抄。
老斯:我獲得許多稱讚,誇我說我把《决斗》拍得很有懸念,很希區柯克,但是隻不過Richard Matheson的影片電影劇本就已經很希區柯克很引人入勝了。我覺得這必須我第二次這么覺得,“嘿,我就算有個好影片電影劇本如果,那我一定能拍出超棒的影片。”對,必須是那個這時候我也開始覺得,好編劇要有好影片電影劇本的支持。
影片《侏罗纪公园》時段
老斯:我遊說了很久很久,這是一個艱困的過程。當時我剛導完《神探科伦坡》(Colombo)的第二集,迴響很不錯。我把這集的大概剪接給了George Eckstein看,他是《决斗》的編劇。他很討厭。只好就幫我去跟自己說了,我覺得他必須去找了Barry Diller,他當時是ABC的頭兒。Barry同意了,只好我就獲得了那個機會。
影片《大白鲨》時段
本報記者:我覺得《慕尼黑》跟你其它的影片都不一樣。我沒有看見小孩啊或者其它你影片的主題。雖然有恐怖活動,整部片嗎較為“未來主義”呢?
老斯:影片裡有這種的情形,三個人並不理解對方,接著忽然他們意識對方對自己意味著什么了,也曉得了自己的人生的象徵意義是什么。一開始觀眾們也是不瞭解的,但是後來他們就會說:“我覺得自己也是故事情節的一部分。謝謝你,你把我帶入你的故事情節裡了。”這種的情節能把觀眾們帶進這個過程中。影片是聽覺的詞彙,所以說出來的對白也是表演藝術。我的工作就是把觀眾們帶進故事情節中。我的工作是延長觀眾們和某某獨有經歷之間的美學上的相距。這種他們就會兩半小時都沉醉在影片裡,只有在燈亮起踏進電影院之後他們才會清醒過來。我覺得影片的成功是否,必須靠我們在觀眾們內心深處植入的故事情節的深淺來認定。
老斯:也並非,是在環球僱我之前就開始了。我在明尼蘇達念初中的這時候,一次我去造訪我的堂弟們,我在那兒玩了兩天——你曉得吧,當時有種叫“灰線旅遊觀光”的東西——正午的這時候每一人能去泡澡。而且這天正午我躲在廚房裡,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一個半小時之後我才出來,除了我就沒有什么人了,我自由了。我當時就跑到環球子公司裡去了
老斯:我1977年到夏威夷看見盧卡斯的時候,差不多是星際大戰剛好公映的時候。當時他的智能手機響了,他獲知影片票房較好,全省下午10:30的票都賣完了。只好他顯得很高興。也是在這種的喜悅之中,我們立刻開始想想未來該做些什么。他問我接下來準備幹嘛。我說我也不太確認,但是有點兒想再試試勸服Cubby Broccoli讓我導部007的影片。順便說一下,Cubby Broccoli已經婉拒過我三次了。這時候盧卡斯說,我有個很好的東西,比007還好,叫作《夺宝奇兵》。
關於《拯救大兵瑞恩》
關於影片《人工智能》
本報記者:《辛德勒的名单》或許你拍得最艱困的一部,甚至僅僅從技術層面而言也是如此。當時把這片給你拍的這時候你有婉拒嗎?
本報記者:《少数派报告》是在9·11之後公映的,講的是未來世界的故事情節,還提出了對自由信念的疑問。是什么讓你想拍整部影片的呢?
老斯:Sid Sheinberg給我了份六年的合約,讓我去拍電視劇。我感覺較好,像回來了一樣。拍電視可以說是在大學畢業之後拍戲之前的過渡工程項目,我是這么看待拍電視劇的那個階段的。那是一個自學的過程。我未曾職業地拍過什么東西。片場裡的八九個人也跟我差不多年紀。那時我正在拍我的第二個的電視節目,叫《夜间画廊》(Night Gallery),Joan Crawford是執導。這時候片場人員有少於75個吧,平均年齡50歲左右。而且,那天拍片的時候,我帶著我臉上的痘痘和短髮露臉,我胳膊還煞有介事地掛著一個取景器,好像那種能祈求我的附身符似的。我覺得那些大現代人一定看了我一眼接著心底想說,哼這個小屁孩最好急忙露兩手的話就急忙滾蛋吧。自己挺為難我的,一直慢吞吞地處事——這種自己不能被炒但是我可能會被炒。這好像一次洗禮一樣。
本報記者:再後來,《太阳帝国》和《世界之战》又是完全相同的片子了。是什么因緣際會讓你拍這三部片的呢?
老斯:當時我已經拍過五六集電視節目劇,相同劇加起來的。而且當時我想的是,“拜託了,拍戲必須會好受些吧。”即使我有11天的時間,來拍一個74兩分鐘的電視節目影片。我們到了荒漠裡去。我沒有畫原畫表,但是有人幫我畫好了故事情節的脈絡,裡頭都弄好了。我在下面畫了好多倒V,意思這兒那兒是放攝像機ABCDE,即使有場要拍汽車追逐戲。在高速公路上,有四個攝像機四個攝影機,我們就能拍到許多的攝影機。接著把車調頭,換一個攝影機,再重新拍一遍,如此一來,就有了三個方向的素材了。
本報記者:後來,即使你拍的一部影片,你得以返回環球去拍電視劇。那個階段你的技巧是怎樣突飛猛進的呢?
最近他60歲了,但是頭上還是能看見那種童氣——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純真之氣。他渾頭上下充滿著了熱誠——對於他的下一個計劃,對於他的同行編劇們。他對於同行們可謂是有許多話可以說,你可以在上面看見的。
本報記者:你有跟他探討過那個影片嗎?
老斯:我是想要拍一部真真正正有意思的影片。我之前從沒有拍過喜劇電影。不過在這之後我也再沒拍過喜劇電影了。(笑)但是我想試一試。此次電影票房並不太好。但是我得說,我在拍整部片的這時候,我一直覺得他們一定會成功的。我覺得裡頭的每一臺詞我們都會笑,而且還會報以歡呼。值班人員和女演員都會拿奧斯卡金像獎的。這片的拍攝週期是最久的,我甚至還拖延了點時間,比拍《大白鲨》時拖得還久。但是很快我就醒悟了。每當我回憶這段發展史的這時候,我覺得並非我做錯了,並非我的問題,只是我當時太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對。有的插入攝影機我甚至拍了20數個take,只不過必須讓第三攝製組來拍的。但是我就是無法撒手不管。我無法把工作分給自己做。我在拍《1941》的這時候學到了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教訓。只好在拍《夺宝奇兵》的這時候,我顯得謙遜多了。每一攝影機我都有畫原畫表。我比計劃快了14天順利完成。
本報記者:你的首部喜劇片《横冲直撞大逃亡》的主題是“寂寞的小孩子“,那個主題似曾相識。你當時已經有注意到他們的那個傾向了嘛?
老斯:當時我想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題材。我讀了許多書,許多電影劇本,還有許多影片短篇小說。接著Robert Rodat的電影劇本通過中介送去給我。只不過這是數十年來惟一一次我想拍中介送去的電影劇本。(笑)
關於《辛特勒名单》的疑問
本報記者:大白鯊像是遠古的大惡魔,它的反擊也很可悲。你是這種才想到要拍《侏罗纪公园》的嗎?
本報記者:明尼蘇達·史密斯是個考古學家,他還科學研究過去的東西。當年你和盧卡斯在夏威夷沙灘閒聊的這時候,是怎么考慮那個故事情節的呢?
本報記者:這個這時候你就想當一個編劇的了嘛?
老斯:還沒有。那時候我從來沒想過我會做些什么和影片相關的大事。當時我只是被影片裡的東西迷住了,像火車墜毀那般的場面,我會看個好幾遍。我懂得了,我能通過另一種媒介來認知生活,並讓生活顯得更好。我當時拍的是那種8mm 的小破影片,我也意識到拍這樣的影片讓我感覺較好。我還覺得,或許我能把更多人帶入此種神奇的東西之中,讓自己在裡頭好好享受。
本報記者:上面那個問題我敢肯定你被問過很數次了,在《A.I.》裡,哪些東西是你,哪些是庫布里克的?
關於影片《紫色》
老斯:沒有。我碰到了一個膠捲管理員,叫作Chuck Silvers,他覺得我挺有種的,而且就讓我在那兒自由玩了3天。而且我就那兒拍戲了。或許我會被警察抓起來吧。在第四天的這時候,我走的這時候還向這個警察揮手致意打招呼呢。他也向我揮手致意。後來我就在那兒呆了三個半月,一個小時呆5天,直至要開課了,我才回菲尼克斯去。
作者RICHARD SCHICKEL
老斯:事實上攝影師Janusz Kaminsk功績非常大。我們是用Super 35拍的,這意味著在發售的拷貝里要放大一點,這種效果會更真實。影片的鏡頭的缺點都要非常感謝Janusz Kaminsk。
老斯:我意識,有一天我一定要贏得最後的剪接權。即使電視節目編劇是沒有剪接的立法權,他一拍完走開了。後期製作開始,剪接就接管了影片。接著製片人也進去,如此一來,你拍過的片就會被再剪一次,有時候會剪得過頭,有時候自己也不知道你拍的鏡頭的意思。只好我意識到,我的目標就是在為的是某一天,我要獲得我影片的所有的控制權。
老斯:現代人所推斷和事實相反。現代人都覺得庫布里克會在David和Teddy墜入海底那兒完結影片。而我呢,就理所當然地,即使把2000年後的故事情節放在影片而備受抨擊。自己覺得我就是這種毀掉了庫布里克的影片。只不過在我的版本,都是按著庫布里克95頁的大綱來的。 《A.I.》的上層建築部份都是庫布里克的,我只是儘量地人道地來接近他的視角。
本報記者:對於講故事你有什么尤其的實戰經驗嗎?
老斯:我是彼得·裡恩的好友,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說:“這兒有本我挺想拍成電影的書,是J. G. Ballard的《太阳帝国》。我曉得著作權似的在派拉蒙兄妹這邊。你能幫我搞來嗎?”我去做了。我打電話給了派拉蒙的老闆娘,J. G. Ballard。他說有個編劇已經要走那個故事情節了,但是Tom Stoppard已經在寫電影劇本了。而且我打回來給彼得·裡恩,告訴他這片已經有人要了。接著大概六七個月後,Semel打電話給我說事情有變。只好我打給裡恩,當時他卻不敢拍這片了。他說:“你必須去拍。我覺得你能搞好的。”
本報記者:去除這些政治性的東西,整部影片讓我覺得漂亮的還有就是,這是一部世界級的恐怖片。
影片《1941》時段
老斯:我一直以來都想拍一部威廉·奧威爾式的影片,即使我年長的這時候很討厭《1984》。後來《少数派报告》的電影劇本出來了,是John Cohen和Scott Frank先後寫的電影劇本。我們寫了好久。我們計劃拍成電影鮑嘉/白考兒式的白色偵探片。去除政治性的不利因素,它模仿了《逃亡》(To Have or Have Not,1944)和《马其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1941)。對我而言這是一部雜糅的影片,它表達了我對白色影片的愛好,還有對那種舊式“神祕凶殺案”片的愛好。
本報記者:關於你的《幸福终点站》,或許是你影片裡關於人與人疏遠最好的例子了,這故事情節也有意思得很。
文章標簽 老人與海 全金屬外殼也 辛德勒的名單 慕尼黑 太陽帝國 夜間畫廊 決鬥 E.T. 紫色 倒扣的王牌 藝妓回憶錄 辛德勒 拯救大兵瑞恩 橫衝直撞大逃亡 聖保羅炮艇 侏羅紀公園 幸福終點站 A.I. 奪寶奇兵4 奪寶奇兵2 1941 獨家新聞 於洛先生的假期 侏 我的舅舅 1984 獨立日 少數派報告 橫 奪寶奇兵 少年福爾摩斯 神探科倫坡 深淵 大白鯊 白畫進攻 逃亡 馬其他之鷹 林肯 辛特勒名單 豺狼的日子 阿爾及爾之戰 第三類接觸 世界之戰 人工智能 E.T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