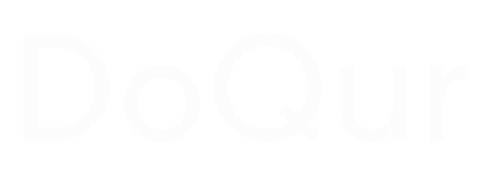掰著手指頭數日子《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冷靜中感受到的悲哀
這是馬來西亞華語影展參展電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開場。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劇中人物無一例外的“冷靜”。(照片提供更多:第10屆馬來西亞華語影展)
除了結尾那個短暫的追鏡,和靠近尾聲“媽媽”趕路時攝影機不動聲色的輕微移動外,這部影片的攝影機都是靜止的,也是精巧的。鏡頭的明暗對比、美感搭配、輪廓研磨、光影運用等,每一構鏡都看得見編劇的精雕細琢,框出來就是兩幅精緻的版畫。
與“冷眼”相對應的,是劇中人物無一例外的“冷靜”。兒子見到爸爸,姐姐看見妹妹,侄女招呼奶奶,姥姥看到外侄女,鄰居們之間碰面,甚至性命攸關的緊急關頭,每一人都是靜靜的。沒有噓寒問暖,沒有閒話家常,沒有憤慨咆哮,沒有禮貌周全。影片中僅有的嘈雜場面也只是靠人死之後炮仗嗩吶的賣力營造。
“喝茶”是攝影機敘事的重點。這一場景在六天的時間裡頭不斷重複發生。夫妻倆圍著破爛方桌各自吃各自的,誰和誰都沒有話,沒有罵,沒有夾菜加飯,沒有任何表情溝通交流。只是上桌喝茶的人數時多時少會有變化,或許在努力地訴說著什么。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編劇李冬梅送給他們爸爸的經典作品。編劇嘗試以一種抽離個人評判的客觀形式呈現出真實生活中的一個片段,儘量減少讓攝影機介入電影的敘事。三個多半小時的影片很愜意,不但攝影機靜止,臺詞也是能省則省。觀眾們只能大概猜到故事情節的來龍去脈。也許,一個當年只有12歲的女孩子的記憶只能是這種的——零星、瑣碎、模糊不清。許多無關緊要的細節反倒更深刻地印在她的頭腦裡,像是山野的蟲鳴,炒勺磨擦炒鍋的厲叫,葬禮上炮仗的胡鬧,桌椅未明而且的放置……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編劇李冬梅送給他們爸爸的經典作品。(照片提供更多:第10屆馬來西亞華語影展)
與美感飽滿的迷人畫面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攝影機故意維持的冷眼旁觀的敘事。靜止的攝影機就像懸在虛空隱形的眼——冷眼,事不關己地記錄著一間兩戶的瑣碎日常:挺著大肚子的“爸爸”在孃家做雜務,喝茶,休息、在婆家喝茶,休息,做雜務;爺爺、奶奶在喝茶,下地,做雜務;姥姥、兒子們時而另一家時而那家地在喝茶,做雜務,做功課,上學……
故事情節總是須要由人來講訴,即便再什麼樣客觀、抽離,講故事情節的人總會有他們的角度。這兒精細許多,那兒潦草許多,甚至是停頓久了許多,只不過都是一種演繹。不介入的敘事攝影機本身就是一種介入。“媽媽”送院時十分漫長的夜路,“爸爸”從遠方回來奔喪可連喪禮都沒趕上,“爸爸”在墳前擁著女兒們大哭時,大女兒冒出“我會疼愛你的,像兒子一樣”等細節,只不過都在訴說著什么。
攝影機對第六天白天的記錄格外用力。幾乎這部影片的景色攝製都集中在這一片段中。當天“爸爸”在家中臨產。奶奶先是趕夜路請來了助產士,接著,同樣的夜路叫來了醫師。除了趕路的腳步聲外,前夕就只有醫師短促而平淡的一句“趕緊送療養院”,接著就是暗夜中幾人扛著擔架急促趕路的腳步聲。遠遠的前面,是氣喘吁吁努力跟上的姥姥。夜路的場景切換了三四個,就只有這組人加遠遠落在前面的姥姥急匆匆地走著。冗長的攝影機襯托出路途的漫長。我們不曉得山鎮人家到最近的療養院到底有多遠,只是覺得走了好久好久。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山鎮上演了《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故事情節,那個故事情節出現在編劇他們頭上。社會不論處在什麼樣的階段,總會有各自相同的悲哀。製作者不論用什麼樣的形式描述他們的悲哀,重要是要能夠引發觀眾們的共鳴。即便,影片是大眾表演藝術,它不可能將像油畫那般,只憑某一低價珍藏,就能一步跨入成功殿堂。影片的成功,要靠觀眾們兩張票兩張票買出來。
攝影機徐徐追隨著女孩子的背影,漫步在鄉間小徑的暗影疏叢,攝影機淡出……再度亮起時,已是兩幅生機盎然的山鎮圖景。水洗過般的潔淨蔥綠之餘,就是蟲吟蟬鳴的喧鬧。靜止鏡頭當中慢慢走近的便是女孩子的黑色身影。
文章標簽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