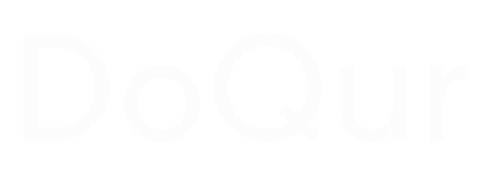影評人|《逃离比勒陀利亚》:聽從內心深處的想法開啟另一扇門
文/王栩
而且,比勒陀利亞殘暴的生存境遇讓安迪走出去的心志愈發堅定。走出去,並非為的是純粹的活著,而是要將非常有限的心靈投入到一個迷人、光明的事業中去。隨著安迪將內心深處的想法轉變成行動,電影的節拍也越發的緊張。這是令人不安的緊張,它以獄警們三次對牢房的突擊搜查表現出情勢的嚴峻讓危險朝臨界點悄然凝聚。此種來自情勢的脅迫對安迪來說,是他經由無聲的啜泣所抒洩的無法寬解的傷感。它反映出安迪內心深處那根繃緊在高壓下的心絃已到了趨近崩盤的邊緣。通過這一故事情節的詮釋,安迪,那個堅強的人,同時也是脆弱的人。堅強和脆弱在一個人頭上交替顯現出來,使得安迪那個人物跟尋常人毫無二致,就是常用的一個會哭、會笑、會被情緒所左右的正在成長中的人。
勝利的尖叫在天際間久久地迴盪,自己笑得那么開懷,那么孩子氣。在這如釋重負般的尖叫裡,搭乘的士趕赴遠方的安迪一行,將踏進牢房的勝利連同曾經的創痛爭相拋諸腦後。自己眼前,筆直的公路指引著自己奔向一個值得期盼的明天。
安迪判刑的那天,就以不尋常的眼光打量著這兒的一切。這兒是比勒陀利亞,一個鋼筋澆築的墓穴,惟一的出路就是開門出去。當一扇通向外界的門被牢牢鎖上,安迪曉得,開啟另一扇門的方式就在他們的信心和毅力裡。
那一刻,隨著電影故事情節的展開,獄警的暴戾,犯人的畏憚,在戒備森嚴的比勒陀利亞鋪張成一幕危機四伏的網,陷身在網中的安迪每一步都走得險惡異常。憑著高超的記憶,安迪記下了獄警掛在胸前的每一把鑰匙的花紋。他用源自車間的廢石料作出了一把把鑰匙,它們能關上從牢房到拘留所正門這段馬路上所有的柵欄。這就是安迪走出去的辦法,有如常人那樣,穿著乾淨的鞋子走出去,而不用以挖地道的形式把他們搞得灰頭土臉,一望而知是個還未脫下囚服的犯人。
——文中看法屬於作者本人,本人文責自負,與發文網絡平臺(含各類門戶網站、高峰論壇、自新聞媒體、社會公眾號)、轉載紙媒、和別人無涉——
安迪不敢挨下去,他要行動,要抓住以自由為代表的一片真正的光明。這光明來自於一個純正的意志,為消除種族隔離而努力奮鬥。那個意志讓黑人青年安迪及其摯友史蒂芬積極主動投身於到非洲人國民大會反種族隔離的祕密行動中,並因而下獄判刑。
作者簡介:王栩。所用筆名有王沐雨、許沐雨、許沐雨的藏書架、王栩326,移居武漢。
電影用“踏進牢房”的象徵涵義特別強調安迪及其摯友絕非尋常象徵意義上的犯人。他和史蒂芬只是背棄了自己的膚色,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黑人至上主義者甚囂塵上的澳大利亞即使對種族隔離的抵抗而蒙難判刑。這是政治對有罪的普通人的操弄,它讓安迪在獄中的抵抗有著明晰的價值指向。此種指向在安迪那天判刑,和丹尼爾同桌就餐時就初見端倪。
那個成長中的人,在通向外界最後一道門難以關上前夕,懼怕地想要重新返回牢房。米勒喝止了他。米勒,無時無刻都想踏進去,帶著對父母的悲傷,帶著對獄警無故剝奪了女兒的探望時間的恨。悲傷和恨共同催化劑了堅毅在米勒內心深處的永駐。安迪的越獄行動裡,踏進牢房的辦法固然關鍵,可支撐安迪將行動繼續下去的動力系統除了意志和引導,還有一份堅信奇蹟終會發生的堅毅的產品品質。堅毅是凝聚心志的內驅力,在它的主導下,堅信他們成為安迪從米勒頭上汲取到的關於應對艱困時世的生存智慧。
端著餐盤的安迪正遲疑著與否同兩個身穿紅色囚服的罪犯趴在一同時,被身旁的丹尼爾推搡著走進另兩張餐桌坐了下來。似乎,丹尼爾和安迪穿著棕色的囚服,同屬於罪犯中相類的一大群。這一大群,和穿紅色囚服的殺人犯們的差別在於,自己不但是獄警眼中的重點監控對象,還是獄警最愛招惹的人。
最後的一刻,獄友丹尼爾又重新點燃了旺盛的士氣。他仿若重拾先驅者的面目,用吸引獄警注意力的形式掩護安迪一行的出逃。丹尼爾終究返回了先驅者的行列,以勝利的尖叫嘲諷著對牢房裡兩名犯人不知所蹤而驚嚇的不知所措的獄警那張蒼白的臉。
獄中,結識了米勒的安迪在前者的引導下,開始著手進行一項不可能將順利完成的行動。那個行動在安迪的腦海中裡具體成型為,既然沒有其他辦法能成功越獄,那就從牢房裡走出去。走出去,讓安迪、史蒂芬,米勒三人達成了一致的共識,為的是自由的明天,行動就從今天開始,從那一刻開始。
(電影信息:《逃离比勒陀利亚》,導演:路易斯·安南,編劇:路易斯·安南、L·H·哈里森、羅爾·格里菲思、安迪·詹金,執導:安德魯·雷德克里夫、伊恩·格林、安德魯·韋伯,愛爾蘭,2020年)
安迪不願象丹尼爾·戈爾德施泰因那般老死獄中。丹尼爾,那個曾經和曼德拉一同站在被告席上的先驅者,在獲刑四十年的徒刑面前,已顯得信念消沉,情緒低落。現如今的丹尼爾喪失了對自由的熱望,只剩下告誡新近判刑的人安分守己的挨下去。
(全文完。作於2022年3月28日)
文章標簽 逃離比勒陀利亞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