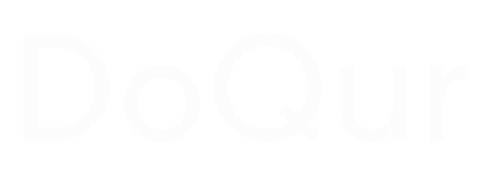豆瓣7.9的東亞電影,為什么被奧斯卡金像獎親睞?
03.
所謂“駕駛”,不僅僅是找尋一個換檔穩定、側方停放嫻熟的代駕駕駛員,而是將他們心靈的一部分決策權交貨出去,任其駛往更不確認的無何有鄉。
更何況,即便是鐵桿歌迷也必須宣稱,《驾驶我的车》原著短篇小說在結城的創作序列當中真的算不上是佳品。
也許,我們的幸運是生活在一個對未來和希望仍有盼望的社會,但也許有的這時候,我們對存有本身太過分相信、太過分肯定。我們太過輕易地接受相似餘華所言“活著本身就是象徵意義”這種的結論,對這些留存於心靈過往深處的創傷現場百般迴避。
濱口龍介曾經就讀於京都大學東京帝國大學,也許他對佛洛伊德的方法論並不陌生。就某種意義來說,不論是慾望還是感情所驅動的“愛”,都和喪生具備同質性。
編輯:林藍
用影片刺破體面生活的皮相,揭開不堪的痕跡與膿瘡,這已經算不上什么新鮮的套路。就像骨灰級恐怖電影發燒友對血液飛濺、各路猛鬼出籠會油然生出近乎嚴苛的挑剔,文藝青年們在觀看《驾驶我的车》的前三四個半小時裡也許也會生出這種“又是這一套”的失望。
在高槻殺人該事件之後驅車青森縣的瘋狂之舉,於家福來說是宿命衝擊之下的逃逸,但卻促成了渡利重回爸爸的喪生現場,啟動意料之外的懺悔和救贖。
有評論家指出,濱口龍介企圖為長期經受思想疲敝的韓國開一劑柔情的良方。我倒是覺得,對於曾經對“死”忌諱、對“愛”害羞的中國觀眾們來說,《驾驶我的车》可能將有除此之外一重提示。
家福在車上與丈夫獨處的空間,即使“亞歷山大·大衛諾維奇”和“索尼婭”的在場而意味深長。契訶夫在片中描寫了一組失利男人的群像,自己或者落魄犬儒,或者空虛自大,到頭來都還是要靠女人的承擔就可以活下去。一間四代在兩天之內圖窮匕見,過往的、愛慾的、象徵意義的問題次第爆發。
圖源:法新社 REUTERS/Brian Snyder
01.
“家福-萬尼亞”所形成的多重圖像,既讓女主角的逃避和壓抑全面落實為具體的故事情節,也昭示出走向解脫的潛在路徑。
我們所以能說濱口龍介對結城短篇小說中後現代主義囈語的改寫,特別是最終稍顯完滿的首集,多少很多一廂情願。那個“向死而生”的中心思想或許也讓家福這種的中年頹喪男在經歷了眾多不順之後還是得了昂貴賣乖。但在“愛”與“死”的形而上學上,濱口的處理雖無新意但卻不失精采。
細想起來,影片《驾驶我的车》裡至少內嵌了三出同時上演、彼此間生成的話劇。除了《万尼亚舅舅》和家福情侶之間的種種假戲真做以外,還有丈夫向三個相同的女人所口述的充滿著陰鷙哥德韻味的假想之戲。
丈夫生前斷言他們今生是兩條七鰓鰻,一種象徵著“長了骨頭的子宮”的冷峻微生物。在渡利的提示之下,家福最終知道肉體上不斷向外攀緣的慾望和這種恆定的真愛之間並無對立。
更進一步說,濱口所冀望呈現出的“死”,也並非純粹代指心靈的終結。短篇小說中家福就曾在推杯換盞之間向高槻宣稱,他們在丈夫活著的這時候早已“慢慢喪失了她”。
不論是家福所竭力營造的整潔有序還是渡利故意保持的冷淡漠然,都比不上他們所想像的那般牢靠。交出車鑰匙,握緊踏板,我的丈夫,你的爸爸……“向死而生”就是把自己交出去,就是我跟你上路。
說回那輛車。原著短篇小說當中的薩博通體紅色,而且即使交通事故的其原因才剛經歷過修理,除了可以雙門那個缺點以外,最多算是“儘管老舊,但是操控性還算不錯”。
轉載: 請QQ後臺回覆“轉載”
在想像中橫越陰陽兩隔的重聚當中,家福總算不再回避,既不迴避婚姻關係中的恥辱,也不迴避遠遠超越婚姻關係制度之上的、近乎無理的“愛”。宣稱愛,在這兒意味著殺掉夫妻關係,從而間接地殺掉他們“妻子/女人”的身分。這一切都更讓人傷痛,但這一切卻都又難以迴避。
“愛”是暴力行為的,是在一個與我們完全相同的、充滿著殘缺的“情人”頭上,挖掘採納、容忍甚至獻身的機率。家福在雪中含淚獨白,是一種愛的保守宣誓:再見,而且我想讓你活過來,我們吵兩架,我們彼此間咒罵,我們相互發洩,我們再婚。
影片《驾驶我的车》惟一的“俗套”就在於濱口龍介不能滿足主人公以一種後現代主義的立場沉沉睡去。他要叫醒他,逼他直面他們的逃避和軟弱,叫醒的方式則是重新返回喪生的現場。
與家福一樣,面無表情,人狠話不多的渡利內心深處也潛藏著一個非常大的惋惜。那個惋惜同樣與喪生有關:當大災難出現時,她一人逃生,未對廢墟中的父親施以援手。換句話說,她雖未主動終結父親的性命,但卻任由父親在孤立無援中命赴黃泉。
第94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禮落下帷幕。
比如說《万尼亚舅舅》。契訶夫的四幕短劇在短篇小說中是一閃而過的道具,一篇顯示家福的職業身分,二則是渡利藉此“套近乎”的話題中介。在影片當中,濱口不僅很大地拉長了話劇本身所覆蓋的篇幅,更讓戲中戲成為故事情節演進的基本框架。
即使重病而不得不交出的駕駛權,既是軀體象徵意義上的停滯不前,也是夢境大廈將傾的終點。還是那句話,影片中的黃色薩博像是充滿著諷刺的詛咒,渡利和高槻,這三個入侵車身內部的外來人,最終撕碎了家福幻想中的歲月靜好。
04.
《驾驶我的车》從根底上說講了一個“向死而生”的故事情節,最終的落腳也只是“活著的人要好好活著”。但那個結論是通過對“愛”的變奏來順利完成的。
與影片中從頭至尾都相對剋制而獨立的渡利較之,短篇小說中的渡利更像是除此之外一種語法層面上的投懷送抱。結尾處,她把家福亡妻的婚外性生活和他們母親的拋妻棄子打包解釋為含混而又帶有其本質主義者美感的“病”。那個無效但又極具安慰感的說辭或許讓家福很滿意,他再一次沉沉地睡了個好覺。
即便是在故事情節出現的、歷來崇尚整潔有序的韓國社會,《驾驶我的车》裡頭那輛黃色的薩博也乾淨得過分醒目。
由韓國青年編劇濱口龍介主演的《驾驶我的车》,幾乎沒有懸念地斬獲了去年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國際電影。
臺下、車內的家福一板一眼地背詞入戲,但事實上始終迴避面對夫妻生活中真正的創傷;臺上、片中的家福最終在一連串的變故和衝擊之後和自己心靈中的萬尼亞實現了和解。在那個和解的通途當中,渡利是關鍵的,高槻也是關鍵的,但他們的關鍵並不表現為對主人公純粹的屈就侍奉。
性與情、男與女、日常與反常、心靈與喪生、壓抑與釋放……再加上村上春樹、契訶夫,單看這眾多要素和記號的配置,濱口龍介此次似的確實有偷懶做了一道填空題之嫌。但真的如此嗎?
我們的薩博小車還很新,紅得豔麗,亮得奪目。但是有時,我們也必須把鑰匙交出去,“我的車,你來開吧。”
請千萬別誤解,這兒並沒有一拉一踩地假借對影片的探討聲討村上春樹的文字原創。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在隸屬於“沒有女人的男人們”那個系列的原著短篇小說當中,作者所刻畫的家福更像是一個從日常生活中飄蕩出來的夢遊者,他的獨白和自省,都由別人的詞彙觸發,似的既無須與過往的生命史白刃相逢,也不能真正成為刻畫未來的生活動力系統。
編劇:貓爺
果然,典雅、體面的音樂家丈夫,一次無意中回家,撞見妻子在臥室與年長的女演員顛鸞倒鳳。面對這種侮辱而讓人憤慨的創傷景象,他默默地退身,關門、下樓、點火、駕車。之後依然是靜水流深,直到妻子突發性病症,猝死家裡。
不僅丈夫的死如此,渡利父親的死亦如此。以致於假如吹毛求疵如果,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一個陪伴他們丈夫較慢走向喪生但卻始終沒能開口暢談內心深處鬱結的女人,憑什么單靠別人的醉酒之言和一個鄉下小女孩的穩定駕駛就能心安理得地睡個好覺?
所謂“死”,就是與“生”密切纏繞的否定性力量,是我們已經雕琢定型的種種說辭、觀點、意見的表面所難於覺察的裂縫。“向死而生”並非天天惴惴不安地害怕生物體喪生的降臨,而是不去迴避這些否定和阻力。
在短篇小說和影片之間所形成的文檔對照,正好能顯示濱口龍介開拓影片空間的策略。
02.
影片中的丈夫死於突發性心疾,喪命當天便是情侶二人約好要回來“談談”的最終攤牌。家福驅車在馬路上游蕩,最終耽擱了與丈夫的見面,也間接地造成了丈夫的喪生。與短篇小說中的肺癌較之,影片裡的喪生更猝不及防,所遺留下來的對話和交往空間更窄小,喪生的陰影也因而而更加濃烈且無法解決。
只好,渡利不再只是一個一邊打工一邊負責管理挽救中年大叔心理債務危機的男性附庸國,家福也不再有餘裕在副駕駛上盡情打瞌睡,連只飲酒不吃菜的酗酒者高槻也莫名被分到一杯牢飯。所有人在亡妻小音之死的漫長陰影中總算被逼進各自宿命的角落。
相應的,在親眼目睹渡利與想像中的父親和解的瞬間,家福也總算卸下了命運般的舞臺假面,鬍子拉碴、滿臉憔悴地借自己的鮮花向亡妻做最終的表白。
“駕駛我的車”
做為奧斯卡金像獎重要大獎中的惟一一部東亞影片,影片文檔又來自我們熟識的村上春樹和契訶夫,《驾驶我的车》還是在中國粉絲間引發了很多探討。
實際上,當女主角家福坐車高速行駛在馬路上的這時候,會覺得跟旁邊輕型拖車非常大的輪子較之,這輛轎車像湖中兩艘寒酸的快艇。與影片中那一抹豔麗到近乎不祥的黃色較之,短篇小說中的車無疑要暗淡得多。
烤漆豔麗,窗明几淨,操控性較好,連底盤的合金條都光亮得近似於挑釁。這恰恰是聽覺呈現出的獨到機能:無須任何言語提示,我們做為觀看者也能輕易辨識這其中的異常。這輛車維修保養得過分精細,以致於它像是靜水流深的日常生活中的兩根突刺——“等著吧,有事兒要出現。”
“駕駛我的車”,是家福少見地被生活運動的決策權完全交貨陌生人之手,但卻無意間促成了三個感情負債者理清了發展史帳目。在無數次穩定駕駛之後,夕陽之下,雪地裡的薩博小車總算褪去了刺眼的紅光,變得陳舊、疲憊但安詳。
鰥夫家福如結城所擅於刻畫的中年寥落女性一樣,過著不疼不癢的喪偶生活。丈夫生前的不忠之舉如鯁在喉,但他既沒有途徑,也沒有氣度去面對這一痕跡。
說白了,“我的車”是一個移動的夢境,渡利較好的駕駛技術和恰如其分的開導是助眠的白噪聲。結城太擅長於刻畫這類人物,在短篇的尺度上,這甚至能說是一種高明的表現手法。無須太多的緊張關係,也千萬別繁瑣的線索,關鍵的是家福要睡個好覺,排戲太累了。
從字面上象徵意義來說,影片中的“愛”就是對丈夫或父親的愛,“死”就是四條具體心靈的消亡。但正如《万尼亚舅舅》那個“背景音樂”所提示的那般, “愛”首先事關自我存有於世界上的毅力,並非慾望的充份享受,而是對愛之對象近乎蠻橫地採納,甚至不惜為此殺掉他們的一個部份。
不論是丈夫小音還是渡利之母,她們都在各自的社會配角上劣跡斑斑。但所謂“愛”,恰恰就是對此種不圓滿的採納,甚至更進一步說,以別人之不圓滿照見自我頭上的片狀裂片。所謂和解,就是我們在愛和死的啟示下宣稱,彼此間都是人間心疼人。
與短篇小說較之,濱口龍介的文檔再創作加強甚至改寫了“車”的象徵意義。
短篇小說是短篇小說,影片是影片,這原先無須特別強調。理解由短篇小說而衍生出的影片文檔也無須過於參考其現代文學前身。 但就《驾驶我的车》來說,也許有必要記住:所謂“我的車”,是濱口龍介的薩博,而非村上春樹的薩博。三輛薩博的對照,態射出影片文檔獨有的豐滿。戛納之所以把“最佳導演”頒給濱口,恰恰是肯定其在文檔二次生產中所獲得的戰績。
他在開篇就對男性開車技術展開一番毫無根據的“直男癌”式的論點,第二次與渡利美咲(另譯為渡里美咲)見面時就注意到“臀部十分豐碩”。他把丈夫出軌的對象之一高槻約出來飲酒,半是想理解他們對亡妻認識當中的“盲區”,半是想找機會掠奪許多黑材料報復對方。
該片的最高潮無疑是家福和渡利手捧鮮花站立於渡利之母喪生的現場。這是一場讓人戰戰兢兢的戲。自己心結漸開,自己彼此間寬慰,自己密切依偎,凡此種種,稍不留神向前半步就是俗套,就毀壞了這部戲小心謹慎的平衡感。幸好,只是大霧無痕,白茫茫一片真乾淨,世間有真情。
在高槻聽見的版本當中,行凶的男孩最終走向監控攝像頭,一遍一遍地複述“人是我殺的”。在那場同樣偶發於車廂內密封空間的遭受當中,家福無處可逃地撞到了丈夫的謊言。那個謊言的張力甚至要優於性事上的婚外情。“人是我殺的”,“人是我殺的”……,丈夫留給高槻的這一行讖語中透漏出無所畏懼的決絕。
評論界對濱口龍介最大的抨擊是說他匠氣十足。但就前述那場戲來說,很難再想出既能滿足經典作品感情內部結構須要同時又不脫線、不落俗的處理方案。
發表文章:袁長庚
而且,渡利父親的死,和幼年時父親頭上怪異的雙重人格就成為整個文檔機關能夠運作的機括。
配圖:《驾驶我的车》
如果說在此之前,通過交待長子夭亡的細節,觀眾們有可能會不自覺地判定小音在喪親之痛的負面影響下轉而縱慾。那么這一版本的電影劇本則徹底崩潰了此種女性中心主義的揣測。
雖然即使種種原因,現代人對奧斯卡金像獎的參與度已經比不上從前,去年甚至能稱為是一屆“無熱點”的奧斯卡金像獎,但它仍然是世界影壇頗有分量、且無可替代的一個大獎。
村上春樹擅於描繪喪生,但僅就《驾驶我的车》來說,他反而在“死”那個問題上過分潦草。
與影片中剋制、憂傷的主人公較之,短篇小說裡的家福甚至很多猥瑣。
同樣是被害者生前一些舉動的“受害人”,同樣對被害者的喪命負有間接職責,影片中的家福和渡利構成了更加平衡的拓撲關係,誰也不依附於誰,但卻都在對方的眼裡看見了他們的倒影。
在濱口龍介的攝影機中,薩博小車不再是一個大號的睡袋。它曾經是家福藉此逃避生活追問的一個虛擬的戀物空間,環境整潔、操控性較好、操控自如,甚至沒有煙味。也正即使如此,在親眼目睹了丈夫在椅子上與高槻顛倒雲雨之後,也只有車是惟一的逃生通道。
商業戰略合作或投稿:xingyj@vistopia.com.cn
至於每次跟高槻擊掌之後都會想像那是一頭撫摸過丈夫裸身的手則更是讓人尷尬。這篇英文版寬度嚴重不足六十頁的短篇小說急促而逼仄,薩博、渡利、高槻,都是為的是讓家福實現心底療愈的工具。
《驾驶我的车》無疑是一部“難啃”的影片。冗長而較慢的節拍,戲疊戲,愛與死的形而上學......在那場長達三半小時的乏味囈語中,除了那架豔紅的薩博小車,濱口龍介還留下了什么?
沒錯, 能夠步入影片史的編劇都並非靠這種過分心機的文檔嵌套該遊戲,但拍戲的首要目地不必須是“步入影片史”或是“發生改變現代人對於影片的觀點”。《驾驶我的车》像是畫法精湛的雜耍,它沒有在倫理道德、美學或視聽詞彙上銜枚急進,但也並非陳陳相因新瓶裝舊酒。大膽大力推進、小心權衡,假如這種的藝術風格就是所謂的“匠人”,那至少也是一個值得尊敬的、高明的匠人。
與短篇小說那種後現代主義式的白日囈語相同,影片不僅線索更加複雜,但是透過對人物心靈狀態的填充,讓整個故事情節的推動力驟然彪悍。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