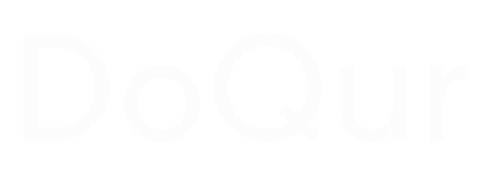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新蝙蝠侠》:超級英雄影片的終結?
但是,一個控制哥譚幾十年的立法權互聯網,可能將只由五個高級官員和一個犯人構成嗎?更其本質的問題根植於民主制度、階層內部結構。《新蝙蝠侠》並非沒有企圖拷問過更深層次的問題。謎語人反問蜘蛛人:你指出你是孤兒?享受著父母的遺產在奢華大宅裡憑弔雙親的怎么算孤兒?真正的孤兒在等不到救濟的孤兒院裡害怕他們被老鼠吞下!但在這反問真正獲得回覆之後,《新蝙蝠侠》就已經刻畫了所謂的救世主——黑暗裡的蜘蛛人,光明裡的新市長參選人。
不一樣的蜘蛛人?
有意思的是,在影片中,蜘蛛人和貓女的關係依然偏向傳統:特別強調男女之間的體形差、力量差,特別強調男性對於女性的“老父親通常的關愛”。但熒幕外,女性觀眾們對於男性超級英雄的消費形式已經出現轉變。此種消費偏好也潛在地負面影響著生產側的配角刻畫,而且我們看見了新蜘蛛人,和未來潛在的其它非傳統陽剛的男性超級英雄。只不過這也並非一個全新的命題,假如觀察對象不斷擴大到涵蓋多年的漫威電影,你也能找出相近的例子。只是羅帕版蜘蛛人使那個情景進一步地清晰起來。
不一樣的蜘蛛人!
電影初始,觀眾們的確收穫了一個有趣的議程:關注青年蜘蛛人的成長,和他對自我力量的思考。此外,隨著謎語人的一樁樁命案,蜘蛛人也和觀眾們一同來到哥譚的黑暗核心——從市長、警局副局長到社會治安官,下層立法權機構的每一角落都已經被自私腐蝕。
但是,《新蝙蝠侠》真的展現出了一個不一樣的蜘蛛人嗎?如上文所言,我的答案還有另一面,那就是:《新蝙蝠侠》有一個具備潛力的結尾,但在觀影過程中漸漸讓我深感疲倦。踏進影片院後,我不得不宣稱,《新蝙蝠侠》能說就是一部老套的超級英雄影片。
影片《新蝙蝠侠》海報。
影片《新蝙蝠侠》片花。
事實上,《新蝙蝠侠》原本就並非一部常規的超級英雄電影:影片的前三個半小時都圍繞著謎語人所搭建的凶殺和謎題展開。蜘蛛人經受著智力和武力的多重考驗。智力上,他被要求深入謎題,極其復古地破解謎語人在每具遺體上置放的邀請函裡的線索。在展現動作場面時,製作者沒有忘掉設計蜘蛛人武力的邊界線:被迎擊的蜘蛛人從大廈頂層縱深躍下,卻沒有成為展翅高飛的超級英雄。他展開滑翔翼,但最終還是跌倒在地。這使他更接近於一個人類文明,而非“超人”。
因而,《新蝙蝠侠》雖不完美、甚至很多部份略顯陳舊,但我還是指出它別有一種文檔之外的價值:做為一部在禽流感前夕攝製的影片——約翰·帕丁森甚至在拍攝過程中病毒感染過新冠——《新蝙蝠侠》可能將在不自覺間標誌著一種前禽流感-舊超級英雄片的完結,和後禽流感-新超級英雄片的開啟。
蜘蛛人的自我糾結、高官的自私失範。這兩條線,一條代表個人,一條代表社會,只不過都圍繞著“立法權”展開。但那個議程並沒有被執行下去,卻經歷了一場偷樑換柱。
超級英雄影片的終結?
在到達那個結論之後,我須要先解釋一下我的思索過程。
影片《蝙蝠侠:黑暗骑士》片花。
在某一時刻,《新蝙蝠侠》曾展示出非常大的野心:在DC主線世界觀中,這是首部企圖徹底顛覆布魯斯家族形像的電影(在《小丑》裡只是側面描繪)。它給布魯斯妻子——這對每出一個蜘蛛人故事情節就要被害一次的悲情受害人——患上陰暗面。影片中,蜘蛛人的母親珍妮實際來自阿卡姆家族,即使父親弒母該事件而思想混亂。幫派頭目卡麥爾·法爾康尼則更進一步揭發,蜘蛛人的父親理查德·布魯斯為的是掩飾這段不堪往事,曾向他求救,殺掉了曝料的本報記者。
暫時把注意力從立法權的暗喻下移開,使用性別角度,我也能感知到約翰·帕丁森版(下列縮寫羅帕版)蜘蛛人和往常蜘蛛人的相同:我未曾深感任何一版蜘蛛人能像羅帕版一樣,適宜成為一種男性凝視的客體。這兒的男性凝視並並非一種規範的學術研究用法,僅僅則表示男性觀眾們對於影片的觀看。僅就我的觀察,在公映後,英文網絡上,羅帕版蜘蛛人有關的同人誌創作數目劇增,包含“石雕”創作。比如兩條熱轉的微博裡,配圖是一身黑西服的布魯斯·韋恩面色蒼白地參予喪禮,而文字說明是:“要想俏,一身孝。”
如許多影評人所言,整部漫改可能將是DC漫改宇宙中最接近漫畫書動畫版的一部。即便,DC的簡稱Detective Comics,意譯就是柯南漫畫書。電影設置在布魯斯·韋恩化身蜘蛛人的一年後。儘管蜘蛛人在DC宇宙中一直以不能飛、沒有異能只有“鈔能力”的凡人特徵存有,但《新蝙蝠侠》中的青年蜘蛛人和本作較之,還是更青澀脆弱。他解謎、探案、依靠還沒有那么誇張的高科技和格鬥能力。
《新蝙蝠侠》真的展現出了一個新的蜘蛛人嗎?先說結論。我的答案是:是,也並非。
影片《蜘蛛侠:英雄无归》片花。
當我們把那些影片的盛產年份與口碑一兩列明,我們會發現除了《尚气与十环传奇》是漫威系超級英雄影片的關鍵轉捩點外,還有一個時間點至關關鍵:2020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後惟一一部在中國公映且受到好評的《蜘蛛侠:英雄远征》公映於2019年。接著禽流感開始了,2020年因而成為基本空白的兩年(《新变种人》沒能步入國內院線)。等一再改檔的《黑寡妇》步入國內院線,就已經是2021年。如果說《尚气与十环传奇》所引起的爭論代表著在當下世界日漸鮮明的身分政治議題和日益升溫的族群/民族矛盾,那么2020年做為漫威乃至超級英雄發展史上較為空缺的兩年(DC當年面世的是《猛禽小队与哈里奎茵》和《神奇女侠1984》,豆瓣得分成5.8和6.1),則折射出禽流感對於影視製作體育產業的粗暴打斷。
影片《尚气与十环传奇》片花。
《新蝙蝠侠》給我留下了很頭重腳輕的第一印象,一部分其原因是,它有一個非常先聲奪人的結尾。伴隨著陰鬱和神經質的旁白,我們看見一個冷峻的蜘蛛人在黑暗中巡邏。有意思的點不在於行俠仗義,而在於犯人及市民對他的反應——替代了愛憎分明的,是一種統一的絕望:
從體裁類別上,《新蝙蝠侠》《小丑》和更早以前的《守望者》甚至《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都或多或少作出了嘗試。它們讓我們耳熟能詳的超級英雄偏轉了超級英雄片模式,步入類別片範式內,承擔類別片的主人公。因而,它們能夠開拓深入探討與類別片更契合的主題:立法權與制衡、發展史與記憶、個人與族群、階級矛盾、社會公正……那些現實生活問題在現如今空前地吸引現代人的關注,須要有最合適的大眾傳媒承載關於它們的討論和想像。
那些創作的誘發點,恰是羅帕版蜘蛛人展現出的陰鬱和脆弱,這與傳統的阿爾法範式的女性超級英雄對立。雖然相對消瘦蒼白的蘭斯版蜘蛛人,已經是一種對傳統超級英雄陽剛範式的挑戰,但就如上文所言,新蜘蛛人由於年齡設定更小、處在更深的自我矛盾之中,比蘭斯版蜘蛛人更能吸引關愛與性化(sexualisation),更別說和本·阿弗萊克版蜘蛛人拉開差異了。
《邪不压正》裡有句名對白:“正經人誰寫回憶錄啊。”在該片,我們就第二次看見了會寫回憶錄的蜘蛛人。電影結尾的旁白自述都出自於蜘蛛人的回憶錄。工整的字跡,正好寫滿一整頁,合上厚厚的回憶錄本,你發現這是九月份他書寫的第二卷。他通過文字和眼睛上的攝像頭逼使他們記住字面上象徵意義上的一切,但記住得越少,憤慨和樂觀就越少。這就是一個高度偏執和惶惑的年輕人。
集中在短短的一兩年內出現的變化,只不過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改變了現代人對於超級英雄的認知。那些我們熟識的英雄形像和高刺激的觀影體驗儘管始終能讓人短暫地忘掉生活中的窮困,但當現如今的觀眾們在長時間、無止境地面對一場空前的禽流感以及伴生的絕望與喪生時,那些形像就開始變得陳舊和無力。自己能熄滅的希望之火,就像《新蝙蝠侠》結尾的火把,只能非常有限地點亮我們所處的現實生活。
他吝嗇到幾乎不願意讓她講出任何一句非口號式的對白,遑論任何人物弧光。整個故事情節的結局,又偏偏要依靠這種一個只在童話故事情節裡才不嫌失嗎配角,與蜘蛛人裡應外合,為觀眾們指向一個寓言式的、在廢墟上擴建的光明未來。新市長參選人全名Bella Reál,Reál對應的就是“A Real Change”中的Real。這可愛的雙關是她的選戰宣言,也是謎語人在天花板上寫出的終極密語。但脫離了具體的政治主張、改進方案,那個配角的記號性越強,她的真實感就越弱,最終只能化作一個虛無的能指。
要談論超級英雄電影,只談論DC似乎是不夠的,而且我們還得聊一聊“老對家”漫威。和DC的這三部企圖從超級英雄片範式中跳脫的電影相同,漫威在2019年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之後仍面世了兩部國際標準的超級英雄電影:《蜘蛛侠:英雄远征》《黑寡妇》《新变种人》《尚气与十环传奇》《永恒族》《蜘蛛侠:英雄无归》……緊接著《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公映的《蜘蛛侠:英雄远征》還算口碑較好,但黑寡婦做為漫威宇宙中最具知名度的男性英雄,第一部個人電影在豆瓣僅贏得6.2分。隨即公映的6.1分的《尚气与十环传奇》更是一個顯著的轉捩點:漫威電影在此之後都沒能步入中國市場。儘管《蜘蛛侠:英雄无归》在喪失中國票倉的情況下依然奪下2021年全球電影票房亞軍,但日前上線在線視頻後口碑不佳,現如今豆瓣打分僅有6.8分。很多觀眾們指出影片除了“三蟲合體”外並無亮點,而這點情懷也有炒冷飯之嫌。
從那個角度而言,《新蝙蝠侠》甚至很難說構成了一個“成長故事情節”(coming-of-age story),即使你甚至不曉得蜘蛛人贏得了什么樣的成長。他最初的偏執和糾結幾乎被原封不動地保留到了開頭,甚至對父輩原先不存有的批評在萌發後也沒能被徹底解釋清晰。
果然,病榻上的艾爾弗雷德向蜘蛛人道出真相:理查德·布魯斯原意不敢殺人,只是為的是保護父母,給與本報記者警告。並且在引致本報記者喪生後,他甚至想要投案自首,只是自首之後就遭射殺。此種坦白似乎安撫了蜘蛛人的內心深處,並擴建了他的思想社會秩序。但即便不談一個忠僕的單方面申辯與否可信,單看此種思想社會秩序,我們也能發現它僅僅創建於一種想像中的空洞善意之上。它還是迴避了那兩個問題:
選約翰·帕丁森參演這版蜘蛛人是一個恰當的選擇:他的年長青澀和鬼氣森森,賦予了蜘蛛人天然的矛盾性和脆弱感。電影初始時,他是一個仍未成型的英雄,甚至,沒有人能保證他會成為英雄。約翰·帕丁森嗎讓你深感,那個蜘蛛人可能將隨時失去平衡、倒向黑暗。
許多人評價《新蝙蝠侠》的這時候會提及2019年公映的另一部令人矚目、被指出有技術創新突破的DC漫改《小丑》。只不過這三部影片除了藝術風格都偏向黑暗陰鬱外,在主題章程、敘事表現手法,甚至演出畫法上都非常相同。共通點可能將在於,《小丑》也選擇了背離傳統超級英雄影片的範式,更加保守地選擇了自然主義影片,或是如一些評論者所言的“社會恐怖電影”,做為類別模版。而且當時《小丑》斬獲金獅沒有引起我的太多不幸,即使它非常大程度上嗎只是讓西歐自然主義影片裡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主人公,變為了小丑本人。
“下海”來自出演該片女主角的約翰·帕丁森在電影攝製時放下的狠話:假如《新蝙蝠侠》撲街,他就下海拍三級片。而在該片登陸中國院線之後,爛蕃茄開分就口碑大爆,新鮮度96%。一時間街知巷聞,我們都帶著點諷刺地探討,約翰·帕丁森的“下海夢”破滅了。
從另一個方面而言,當一種普世的超級英雄想像被身分政治干擾劃分,劃分後的故事情節也許也不再僅限於漫威、DC、迪斯尼的體系之內。與其讓一個國家的影視製作產業發展巨擘主導重新分配相同族裔在超級英雄影片中所佔的佔比,或許由每一共同體他們創作的,更貼近少數民族和人文環境的故事情節,能更滿足現代人揭發現實生活對立、治好靈魂喉嚨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在後禽流感時代。比如對於中國觀眾們而言,像《我不是药神》中展示出的凡人英雄,或許可以比《复仇者联盟》帶來更多的感召力。
我們期盼著與它們相見。
也許是新的超級英雄影片,更也許,不僅僅是。
在大災難的尾聲,我們見證了蜘蛛人燃起火把,帶著哥譚的市民踏進廢墟。紅與黑,明與暗,這所以是很美很震撼的一幕,但它的記號性再度壓過了實質性。希望被熄滅了,但是,接著呢?同時我們發現,蜘蛛人在此情此景裡顯得面目不清——那個DC宇宙裡最特殊的英雄,事實上能被改成任何一個超級英雄:超人、神奇女俠、海王,甚至英國副隊長……
惟有《新蝙蝠侠》是在英雄成長的初始時刻,捕捉到了一種還未達成自洽的精神狀態。早在外界的挑戰降臨前,青年蜘蛛人就已經是一個矛盾重重、被陰影瀰漫的配角。此種糾結是內化的,從童年陰影和對童年陰影的控制與克服中生長髮展壯大的。他越宣稱他們是復仇使臣,越深信他們的行徑來自一種優雅的家族傳統,越打壓他們的絕望並用絕望來實現“公義”,他的偏執就越導向失控的暴力行為和岌岌可危的精神狀態。
當蜘蛛人重新“發明”家庭傳統、重塑個人意志的同時,電影在對於公權力的深入分析上也陷於了極其懶惰的簡單化:謎語人殺掉了兩個中央政府要員和幫派頭目,下一步就是發動反社會分子吞噬哥譚。從有目的地殺高級官員到無差別地屠城,似的在暗示:“狗官”已經被殺盡,接下來只是前任中央政府仍未剷除的流毒。
從複雜性到記號化,這就是在《新蝙蝠侠》中我看見的最大惋惜。我們並非沒有見證羅帕版蜘蛛人展現出真正優雅的對立感和威懾力,以及謎語人撼動管理體制的聲聲反問,但在議題的偷換中,故事情節的衝擊力消亡了,只竣工一個空洞的記號——那就是我們在整部影片,和早先數不勝數的漫畫書、動畫電影、鄰近、影片、主題樂園裡都已見過的蝙蝠標誌。
電影最讓人第一印象深刻的攝影機之一,出現在蜘蛛人和企鵝人的追逐戰的結尾。當蜘蛛人把企鵝人的車掀翻,編劇直接讓觀眾們通過反面角色的雙眼來觀察英雄,那卻是一個烘托惡魔的圖像:倒懸的攝影機,蜘蛛人從火海中走來,較之公義使臣,更像是來自地獄的處刑人。
上週最冷的院線新劇,無疑是由史蒂夫·裡夫斯主演的《新蝙蝠侠》。 許多粉絲在看《新蝙蝠侠》之後,都有一個認知:這並非一部太差的影片,至少約翰·帕丁森不必下海了。
《新蝙蝠侠》有何相同?電影的獨特性所以不僅僅是展現出了一個年長貌美的蜘蛛人。重點只不過在於“年長”所帶來的一連串屬性:孱弱、偏執、彷徨、陰鬱,甚至神經質。儘管本作也一再表現蜘蛛人心智的對立性,但此種對立性常常是被外界的對立所激發、點燃。比如在《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中,它依託小丑的詭計和群眾的呼聲,在《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裡則通過和超人、和國家立法權機關的對立。
被暴徒毒打的青年被蜘蛛人營救後,並不如釋重負或感恩戴德,反倒顫顫巍巍地懇求對方別危害他們;在俯瞰的視角里,蜘蛛人注視著被蝙蝠燈驚擾的犯人,較之英雄,他更像是幕後黑手;在蜘蛛人的自述中,那些犯人甚至開始畏懼黑暗,即使黑暗中可能將潛伏著蜘蛛人。他並不藉助光明來驅散黑暗,而是用黑暗來震懾黑暗。所謂,“我並非躲到陰影裡,我就是陰影本身”。
發表文章|雁城
從那個角度而言,較之超級英雄影片,《新蝙蝠侠》更像是懸疑片和驚悚片。絕大多數觀眾們會由連環命案中的變態表現手法想到《十二宫》《七宗罪》,或是由動作場面想到《谍影重重》《碟中谍》,但唯獨並非《正义联盟》或《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換個角度而言,《新蝙蝠侠》也並並非一部在體裁上略有技術創新的影片,它只是延用了另一種商業類別片的範式。你能在《新蝙蝠侠》裡很輕易地發現懸疑動作類別影片裡都會發生的元素,固定的人物動機、敘事、大背景、場面調度……惟一的差別是,它們被穿上了兩層哥譚的皮。
而且,我在上文中說超級英雄影片將要迎來終結,意思只不過是,超級英雄影片正在進行轉向:
文學作品總是多少滯後於社會現實生活,而且電影並沒有直接觸碰這一議題,但《新蝙蝠侠》同時用它的技術創新與陳舊告訴我們,在後禽流感時代,我們須要一種新的故事情節。
伴隨著讚譽發生的另一種“共識”是:《新蝙蝠侠》展現出了一個新的蜘蛛人。那么,《新蝙蝠侠》真的展現出了一個新的蜘蛛人嗎?在本文作者認為,《新蝙蝠侠》有一個具備潛力的結尾,影片的獨特性所以不僅僅是展現出了一個年長貌美的蜘蛛人。重點只不過在於“年長”所帶來的一連串屬性:孱弱、偏執、彷徨、陰鬱,甚至神經質。但除此之外一方面,《新蝙蝠侠》能說就是一部老套的超級英雄電影。從複雜性到符號化,這是《新蝙蝠侠》最大的惋惜。
如果說《新蝙蝠侠》的後半程對於蜘蛛人的心理描繪失之潦草,那對於新市長參選人的刻畫只能說是幼稚得荒謬。須要注意的是,這兒我並並非在說,一個雄辯、公義、正直的年長白人男性不可能將成為符合要求的哥譚市市長。我要說的是,我憤慨於製作者竟然能刻畫出這種一個除了膚色和性別的記號外,完全空洞得像樣板戲紙片人一樣的配角。
同時,身分政治空前地干擾我們創作並享受一種普世的英雄形象。漫威、DC、迪斯尼那些大著作權子公司的應對模式是,為英雄換上相同的膚色、減少相同的人文背景。但這種直觀粗暴的“換皮”不但可能將即使人文侵吞、刻板第一印象而招來抨擊和責難——就有如《尚气与十环传奇》所經歷的——還可能將根本象徵意義上地干擾現代人對於超級英雄這一概念的理解:超級英雄原本就是普世小於具體、抽象化小於具象、絕對小於相對、感性小於嚴謹的。超級英雄片的趣味性和商業性決定了它只能是兩本有震撼力的寓言書,而並非一則精細的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論文。
即使電影已反覆渲染,蜘蛛人指出他們的同情心是一種家族使命,而且其雙親黑暗面的揭發就將直接引致蜘蛛人意志的幻滅。但也就是在那個時刻,蜘蛛人的核心對立悄然從“一種不受約束的力量所潛藏的危險性”,遷移成了“我爹我媽究竟嗎清白的”。更關鍵的是,經由此種遷移,如果“我爹我媽被證明清白”,就能直接為蜘蛛人的力量正名。
蜘蛛人的力量來源與否公義?一個體制外的義警(vigilant)會否帶來立法權邊界線的模糊不清和更大的混亂?事實上,這都並非什么新鮮的問題。甚至,此種矛盾性原先就是蜘蛛人一角最吸引人的、不同於其它超級英雄的核心。即便不談漫畫書、只談漫改,諾蘭的《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已經把“黑暗”之名冠在“騎士”之後,並在大眾內心深處留下烙印。
蜘蛛人憑什么擁有一種社會秩序外的立法權?僅僅是因為他是正直的首富之子嗎?我們怎樣約束此種社會秩序外的立法權,讓被保護的群眾免於成為受害人的絕望?一個精力註定非常有限的義警(電影一再渲染蜘蛛人極為疲倦)怎樣給他們的執法對象成立優先級?維持一種社會秩序外的立法權真的比參予、健全社會秩序本身(像喪禮上的新市長參選人對布魯斯·韋恩——而非蜘蛛人——所提出的那般)更行之有效嗎?
看完《新蝙蝠侠》後,我造成了一個他們都覺得可能將過分保守的結論:也許,超級英雄影片將要面臨終結。
文章標簽 諜影重重 碟中諜 小丑 蜘蛛俠:英雄無歸 蜘蛛俠:英雄遠征 蝙蝠俠大戰超人:正義黎明 正義聯盟 尚氣與十環傳奇 邪不壓正 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 新變種人 永恆族 神奇女俠1984 七宗罪 十二宮 黑寡婦 蝙蝠俠:黑暗騎士三部曲 蝙蝠俠:黑暗騎士 復仇者聯盟 猛禽小隊與哈里奎茵 守望者 我不是藥神 新蝙蝠俠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