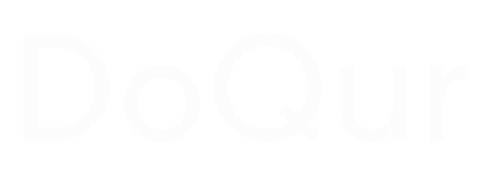12歲小孩將雙親告到法院的背後,有四個不得不說的其原因
故事情節出現在伊拉克的一個貧民區,12歲的贊恩做為家中的次子,為的是養活一屋子裡的兄弟姐妹,被迫在雜貨鋪做童工,贊恩很愛他的姐姐薩哈。但是薩哈很快就被無情的雙親買下居心叵測的雜貨鋪老闆娘,贊恩傷心地離家出走了。他碰到了正直的單親父親拉羅斯,自己互相扶持著度過了一小段平淡的時光。
贊恩的養父母,不但沒有盡到基本的扶養、基礎教育權利,相反,自己用咒罵、暴力行為取代愛與關愛,做為反面教材,以一種極為直觀粗暴的養育形式給小孩樹立了極壞的榜樣。
在和平二十世紀,伊拉克被譽為宜居的天堂,但是在內戰二十世紀,它快速淪落為混亂的地獄。
在一波三折的故事情節裡,贊恩小小的皮膚忍受了太多的苦痛:無法上學、做童工、家暴、姐姐被買下、被煎熬致死……
在法庭上,贊恩說道,我希望大人聽我說,我希望,無力扶養小孩的人別再生了。我還記得,暴力行為、羞辱或毒打,鏈子、管子、皮帶,我聽過最柔情的一句話是“滾,婊子的女兒”、“滾,你這廢棄物”。生活是一大堆狗屎,不比我的鞭子更值錢,我住在這兒的地獄,我像一大堆腐壞的肉。生活是個婊子,我以為我們能搞好人,被所有人愛,但天主不希望我們這種。
在發現姐姐初潮之後,早熟的贊恩就很害怕雙親會快速讓她嫁人,只好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護著姐姐:給姐姐洗內衣、買衛生棉、甚至謀劃著帶姐姐投奔,但是,雙親還是發現了自己的祕密,粗暴地把姐姐送來了麵包店老闆娘家,任憑贊恩發瘋好像揮動著拳頭制止,也絲毫不起作用。心愛的姐姐被母親搶走了,爸爸還在一邊咒罵著贊恩,這直接激發了贊恩的逆反心理。特別是當贊恩曉得姐姐被惡人老闆娘煎熬而死時,內心深處的怒火再也難以打壓,他這一次學著跟雙親一樣,以暴制暴,直接拿起斧頭衝入了撒旦……
《何以为家》是一部由伊拉克、比利時和英國聯合制作的喜劇片,製片人時間長達三年,編劇和團隊通過很強的同理心、耐心向觀眾們展現出了伊拉克底層社會的現狀。整部影片贏得了71屆戛納影片節的評委會大獎,豆瓣四十多萬人給出了9.1的高分。
1. 水深火熱的社會環境
《何以为家》是影片在大陸公映的片名,本片本名為《迦百农》(Capharnaüm)。迦百農在舊約中是耶穌基督佈道的終點,在這兒曾經出現過許多輝煌的故事情節,但最後卻成為一片廢墟;除此之外,在法文中,“迦百農”意為無序和混亂。這三層涵義與影片所反映的現狀及主題都是高度契合的,
伊拉克是一個隱藏在群山之中的小國,東臨黑海,東、北部與敘利亞交界處,南部與巴勒斯坦為鄰。
贊恩一間生活的臥室逼仄狹窄,近六個兄弟姐妹要擠在兩張木頭上睡覺;屋裡除了一個破爛的椅子,幾乎找不到其它傢俱,早上沒有電燈,一我們人只能靠蠟燭照明;贊恩做為次子,無法去上學,他要通過去小賣部打零工財政補貼家用,還要帶著哥哥姐姐去街上賣自制飲品,每當校車從街上路經時,他只能用渴求的表情多看幾眼;在街道上,廢棄物成堆、住宅殘破,少女們吸菸、打架、橫衝直撞……
“自我”是從“本我”中漸漸分化出來的,它督促著個體遵從現實生活,以合理的形式來滿足市場需求。當贊恩的雙親把姐姐搶走了買下面包店老闆娘時,贊恩充滿著了憤慨和恐懼,他一怒之下離家出走了。當贊恩獨自一人扶養兒童約納斯時,面臨被房主趕出家門、買不起奶粉、吃不飽飯、等不到好心人等一連串問題,他不得不選擇將約納斯交予人販子,那般至少能給小孩一個正常的成長環境。
這一記重重的耳光,抽在贊恩雙親臉上,也落在了無數生而不養、養而不教的雙親頭上。贊恩跳出了幼兒的視角,他比孩童更清晰、更明瞭地看見了雙親無休止生育背後帶來的一連串社會問題,他控告的不僅僅是他們的雙親,而是社會的不公正,他選擇揭開他們的傷疤,給全世界上了一節寶貴的教育課。
贊恩的飾演者並並非專業女演員,他確實出身於敘利亞的僑民家庭,但是電影的絕大部分故事情節都是他親身經歷過的,而且他無須演出,就足以撼動人心。編劇在電影最後,給了贊恩他夢寐以求的居民身份證,贊恩總算笑了,這個微笑純真、燦爛而幸福。
對於贊恩來說,他的“本我”只不過就是一個12歲的小小少女,渴求跟同齡人一同上學,一同嬉戲。在贊恩離家出走後,他被蜘蛛人打扮的老人家所吸引,在溜冰場裡,他洩憤通常地扒光了公共設施中男人數學模型的外衣,那些都是贊恩頭上幼兒意識的彰顯,溫柔、唯美、無邪才是自己那個歲數應有的樣子。
儘管電影總體基調較為壓抑,但在恐懼中依然散發著光芒和希望。就像《何以为家》的導演Mousanar所說,
入選奧斯卡獎的影片《羁押》前段時間引發了廣泛熱議,三名年僅六歲的小孩將一個兩歲幼童拐賣至水電站,凶殘槍殺,在獲釋之後兩人拒不承認、互相推卸責任。這三個小孩的表現更讓人毛骨悚然,在自己背後都有一個冷漠的原生家庭,雙親從來沒有教過自己是非對錯。
1943年,伊拉克正式獨立,設立伊拉克共和國,金融創新、對外貿易、交通等行業迅速經濟發展,經濟漸入佳境;但是1975年,伊拉克國內即使宗教信仰派別鬥爭,爆發了一場長達15年的戰爭,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直接引致近90萬人流離失所;再加上阿富汗、巴勒斯坦的陸續侵略,大量僑民如潮水般湧向伊拉克,徹底把伊拉克變成民不聊生的人間地獄。
“超我”是人格結構的最高層,它遵從倫理準則。在電影最後,獲知父親又一次懷孕了,贊恩難以接受愚昧的雙親害死姐姐之後,又將有新的心靈重蹈覆轍,這一次,他決定控告他們的雙親。贊恩長大了,他徹底擺脫了幼兒意識,知道了個體的掙扎是微不足道的,他選擇借用法律條文來抨擊和懲處這些無知、無能的雙親,以此增加悲劇的出現。
看見正處於花季的孩子們身處這種水深火熱的社會環境,不得不在泥淖裡摸爬、掙扎,真的讓人揪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但是好景不常,拉羅斯很快就即使沒有身份證件被警員拘押,走投無路的贊恩只能再度流浪。此次他準備去丹麥(僑民自然保護區),當他偷跑回來取他們的身份證明時,卻不幸獲知了姐姐薩哈的噩耗,憤慨的贊恩打傷了雜貨鋪老闆娘,旋即獲釋判刑。贊恩起訴他們的雙親,他希望所有沒有養育能力的雙親都無法擁有小孩。
整部影片改編自真實故事情節,藉助近似於記錄片的攝製表現手法,向觀眾們真實地揭發了底層群眾的生活狀態,那兒充滿著了飢餓、貧困、混亂、無知、暴力行為、犯罪行為。藉由攝影機,我們清晰的看見了這些人眼裡的麻木、苦悶與恐懼;藉由劇情,我們看見了在宿命面前,有人讓步,有人奮起抵抗。
2. 一塌糊塗的原生家庭
在贊恩雙親眼中,兒子是工具,須要通過出賣勞動力換取酬金,女兒是物品,能通過買賣抵扣租金。
沒有資格做雙親的人成為了雙親,這是極其可怕又可悲的事情,自己無一例外成為了小孩悲慘遭遇的始作俑者。
贊恩那個配角是三維而複雜的,他在壓迫中有抵抗,在抵抗中有讓步,在亦正亦邪中苦苦掙扎。
那個少女既沒有獲得任何愛與保護,也未能保護好他們所愛的人,生活沒有給他絲毫喘息的機會,在幻想和現實生活的撕扯下,少女爆發了,他在拘留所裡發出吶喊,生而為人,何以為家。
便是殘暴的社會環境催生了這種一大批意外的人群,使得自己在生活面前,流離失所,在宿命面前,無可奈何。
天下之大,何以為家?身在井隅,心向星光。
放走尤納斯之後,贊恩的表情徹底暗淡了,
3. 永無止境的自我掙扎
晚期的養育形式會負面影響小孩神經系統的高分子模式,甚至會負面影響神經系統相同部位的體積。小孩漸漸顯現出來的意志品質和選擇的能力是由家庭中的獨有關係決定的。
古語有云,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雙親和家庭是對孩子負面影響最大的不利因素,沒有之一。
贊恩的遭受更讓人可憐,他的正直更讓人感動,他的堅強更讓人欽佩,但是他並並非個例。在火星另一側,有無數個像贊恩一樣的小孩子,在炮火和飢餓中艱困生活、負重前進,誠然,自己的悽慘宿命與社會環境、歷史背景密切相關,我們須要持續地敦促愛與和平。除此之外,是什么引致那些本應在陽光下歡樂成長的孩子,走向暴力行為、犯罪行為、反社會的不歸路,自己行為背後的深層次緣由和動機更為值得我們關注。
他放走尤納斯,就像雙親放走姐姐一樣,在現實生活面前,他毫無還手之力,他慢慢地將社會同化了。
在《原生家庭生存指南》一書中,安德魯·約翰教授表示:
當贊恩提出他們想去上學的心願時,父親粗暴地打斷,婉拒了他的請求,母親則一反常態的支持贊恩,她的理由是,假如贊恩去上學,能把幼兒園發給小學生的軍用物資帶回家,增加家庭經濟負擔,但是,贊恩能上午去幼兒園,下午去麵包店打零工。
贊恩在那些意識中掙扎,在宗教中維持著正直和慈悲,讓我們在悲苦的生活中看見了人性之光。
一方面,伊拉克也正在經歷著從輝煌走向衰敗的時期,另一方面,底層群眾的生活確實是混亂不堪、毫無社會秩序的。
即便你深知你發生改變沒法任何事,但你還是能夢想你做獲得。人類文明的進步靠的是夢想,而並非犬儒主義。
贊恩的雙親並沒有固定工作,他們在殘破不堪的別墅裡養著近六個小孩,那些小孩都沒有合法身分,但是做為次子的贊恩,連自己的出生日期都不曉得,他12歲的年齡是在獲釋判刑後醫師通過牙齡推測出來的。
如果說之後他還在為宿命苦苦掙扎的話,那這一次,他完全地向宿命讓步了。
在心理動力系統論中,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提出,意識中的自我、本我、超我三部份共同組成了完整的心智,本我是人的本能,超我是理想化目標,自我則是兩者武裝衝突時的調節者。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