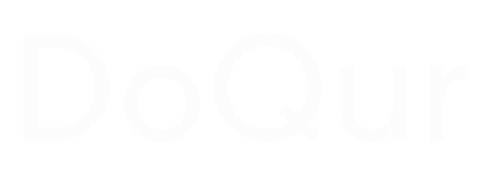放之《四海》皆不許:一場宿命新寵的必然債務危機
不許之三,就是對日常生活的認識和理解的完全失控,以男女主抵達深圳為例:深圳在韓寒眼裡,等於什么?等於面試官必然隱形性別歧視男性,等於老闆娘必然要求女主陪男用戶飲酒,等於女主尋尋覓覓也只能找出服務生的工作——如果說這是韓寒對小人物艱苦生活的僅有想像,只不過大可建議他留意新冠病人底層流調軌跡——會有誰在這般為異鄉生存必然已經一地雞毛的這時候,不選擇為化解基本生存問題抱團取暖,而是眺望一番霓虹燈,感嘆幾陣高樓大廈間的風,接著揮手致意說“等我找出工作了,我們再到天橋見面”?會有誰在妙不可言的巧合下獲得工作,預支薪水後,面對大筆負債和基本吃穿住行問題,先給對方買兩條戒指並且放進杜塞爾多夫裡?
文藝(胡言亂語):迷人的小姑娘在湖邊仰面告訴男主,“你會不能對著星空問問題?”但是就其之後所問出的問題上看,我倒覺得既然沒問出什么有價值的問題,就不建議她拿星空當淘寶客服這么聊。
至於製作者怎樣突破智力競爭優勢的問題,以我認為,個人的一生即使窮盡,也頻寬極窄,因此大量閱讀維持閱讀,對於人自身的深度和廣度極為重要,遊遍各地的眼界亦然。但是摸爬滾打,出賽與生活短兵相接也要緊得很——但是,發出這三種動作的,常常是兩撥人。
很直觀,豆瓣5.6,估算還會低,故事情節也很直觀:兩對迫於生活從島上投奔的青年男女,在走進深圳後,互相為對方犧牲他們而天人永隔——當然,這種的歸納是在我刪掉了大段交待女孩和母親、和島上兄妹、和摩托徒步的蕪雜情節後。之所以能刪掉,是因為並沒交待出個所以然來,更惋惜的是,倘若把對前述的那句對故事情節的歸納刪掉,整部電影也整整長達一個半小時有餘,更更惋惜的是,還毫不妨礙被視作另一部片子。
蒼白(美):劉浩存不論觀眾們緣怎樣,個人以為,都是韓寒的天作之選。除了湖邊長大的她得以倔強維持了編劇執念下的煞白以外,陽光的UV也決不能晒透她的純潔感,從外型認為,這種一目瞭然的清白小姑娘才配得上男主一腔孤勇地為其償還債務。
這么想想,他走老路,他們跟他們致敬,倒也算了,只是八十三,那個今年春節檔的高車費定價策略,放之《四海》,變得更不許了。
那就不妨往遠了翻翻戈爾丁《蝇王》裡的島,往近了翻翻三島由紀夫的《潮骚》——前者用抽象化的故事情節把人性的逼真寫得一乾二淨,後者則是小說家按捺了小說家一貫的坎坷絢麗,用浪花邊緣泡沫般灰白而潮膩的筆法寫了島,和島上的青春之戀。
三部曲之四,仍然是島,選景組應該熟門熟路,但是此番島上的交通卻神祕莫測——男主他爸登島坐的輪渡,變得此島路途艱澀、一處困城,因此數月也不見他登島一次;隨著男主和男孩離島是坐筏子並馱著三輪車,再度認證了其惟有陸路可為;但是,警員和討債的要前來深圳找男主的,卻輕鬆兩輛順風車搞定,且“聊了一路,相談甚歡”——既然公路交通這么行雲流水,那男主為什麼不開車帶著女主返回?哦,等掌握了全劇的基本邏輯你就會知道:交通攻略沒所謂,要緊的是能姑息這個一葉孤舟,漂向茫茫衛星城的攝影機,還有,必須要能插的上這個槓上順風車的梗。
之一:失焦的島嶼。
◎大寒
上了自然主義的山神廟,卻最終只能在青春痛苦現代文學中落草,能看見的,只有韓寒的全面失焦但又困獸猶鬥。
在這一點上,韓寒拿世故當理性,拿聰明的餘暉當開悟的霞光,只不過是任何一個生活的幸運兒在成熟期都難踏入的境遇,就像飽食終日者,日益鼓出來的從來是腰圍而並非關節一樣,倒也無關他是並非個製作者。
對於創作而言,要么談談變化,要么談談永恆,最好是在變化中談談永恆,但就是千萬別談談文藝,即使沒有下面三點,文藝那個東西除了矯情以外,一無所有。
只好,更令人不安的是,片子裡頭流露出一種對電影票房的半推半就,卻又隨著拉來一票戲劇明星和撒鹽般撒梗,沉積戲劇元素並把沈騰全面剪進片花而昭然若揭,更顯露出世故的個性來。
不許之二,必然是人物,而其中最好辨別的標誌就是,對於人物的原生家庭一概用極簡方案:男主母親離島成婚,男主就是無根之子,女主和弟弟相依為命,也是喪父(留下兩張海上經營許可證),至於男主的車手好友,所以也是萍蹤俠影無來無往,所以,關於人物,更值得看一看韓寒一以貫之的對男性人物的審美觀關鍵詞——
但是,拍成電影這種並不不幸,即使這是一場屬於宿命新寵的必然債務危機,已經來臨也必將來臨:不關心小人物而拍小人物,不瞭解真實世界而傳遞世界觀,明知山有虎,或就嗎不想去明知山——儘管資本及後,願賭服輸,只是絕大多數生活優厚者的老路,就是招安他們的同時又矇騙他們:談商業的這時候聊情懷,該真摯的這時候談買賣。
提及“世故”二字,是因韓寒已經處於了自覺早已“理性”的年齡。只是理性和世故的界線一線之隔,只是絕大部分孩童常將後者混為一談成前者,並以此為傲——如果說前者指向更遠處的思索、更深刻的象徵意義,那後者則唯以客觀環境的趨利避害是瞻,只可惜,放大在了《四海》中,更激化了真摯的全面退潮和想像力的逆水行船,結果商業上也全面崩壞。
如果說韓寒至少把他們現實生活中討厭的F1孤島故事情節兄弟情英雄主義甚至那本封面字號碩大的《麦琪的礼物》一股腦塞給了男主之外,那他幾乎就把一個想像程度僅限在高中男生視角的女生人設給了劉浩存,但是這一次,又因毫不走心,還加送了一股中年大叔的異性審美觀媚俗——《四海》裡的女主,其本質上和(中年)油膩女性典型審美觀下的“白瘦幼”沒什么差別,其實套了個文藝濾鏡而已。但是,恰也便是即使苦凹出來的青春茶湯上漂著兩層厚厚的油花,讓全劇人設又陷於了既不夠純又不夠村的尷尬現場。
是的,就是這么隨性,所以了,這又算不算對島嶼生活的一種不拘泥,必要的“抽象化”云云?
脆弱(蠢):這種外貌白淨的小姑娘還要配上才藝上的白淨,比如匹配上“服務生”的身分、“沒有一技之長”的個性,並在如果聖賢才可以維持兩半小時不看智能手機的當下,就是偏不曉得飯店“含早”的意思是含“午餐”,更能因不曉得房卡怎樣刷開,在飯店門口坐足一夜。是啊,從內在認為,這也是個抹防晒霜抹得連對腦細胞維持蒼白也未曾落下的人設。
很難想像,一個對人物喪失除記號和梗以外的想像的製作者,怎樣積極開展創作?一個對男性人物只有淺白理解,更像是網購了一個手辦的編劇,又嗎該去涉足一個和“真愛”相關的故事情節?
至於《四海》的“島”么——用畫鬼的筆墨嗎畫了個鬼,那就嗎是畫給鬼看了。
然而,要當造物的新寵,不免要付出一點代價的,但是較之韓寒筆下企圖去締造的這些人間百態的真實境況,這已真算是奢侈至極的苦惱了。更何況,世間又有多少牆壁並非loft層高,而是天高地遠的大師?
但換言之,他又即便是個製作者,其實似乎卡在了心滿意足的個人生活和粗糲不堪的真實生活之中,騾子穿不過針眼也不見得那么想沿著針眼罷了。
至於電影票房口碑雙慘敗——大過年的現代人接受沒法“悲劇”是體面的第二藉口,所以萬靈的,是還能打張“難以和庸俗戲劇爭奪戰觀眾們”的氣憤牌,只是理由總是低成本的,既然拍成電影這種,倒不妨實事求是,先來看一看“放之《四海》皆不許”都“不許”在哪裡?
固化了,不論是即使憂患的磨損還是閒適的寵溺,總之都是習慣了,都是經驗談,說穿了,也就是“寬敞圈”的變體:對生活不再有發自內心的興趣,對別人他事亦然。只是韓寒錯判了天分和2022年的影片水準的時差問題,也就有了《四海》的格格不入和全面脫軌——
做人有兩條路:一路太順等於一路塌方,雲裡霧裡;一路不順又等於終將世故,雲裡霧裡——顯而易見,韓寒屬於後者,但是他把新劇《四海》拍得倒並非雲裡霧裡,而是直接拍進了海里。
而這兩撥人,在歲月蹉跎之下又將各自畫地為牢,更會以為各自虎踞龍盤了全數世界,掌握了生活的真正真理,只是其本質上殊途同歸,都是一回事:都固化了。
是的,全劇之中,一切眾生公平:都是韓寒的記號,其實以女主為甚而已。而在拍男性已經大咧咧就拍得出結論《爱情神话》的國產電影當下,《四海》對男性人物的立場與其說不友好,不如說漠然和過時。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