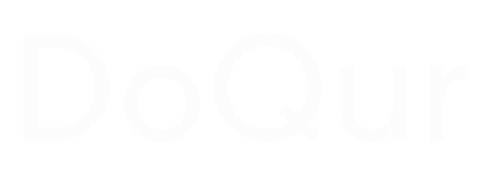相媲美《海上钢琴师》,被整部口碑爆棚的新劇整破防了:唯音樂創作,能叫板宿命
整部《盲琴师》由立陶宛殿堂級編劇馬切伊·佩普日察主演,三冠影后彼得·奧格亞歷克斯參演男主,橫掃立陶宛數個影展大獎,被評選為可相媲美《波西米亚狂想曲》《海上钢琴师》的佳作。
醫師對米耶特病況給出的這些解釋,就是較好的側證。
就在前兩天,又有一部以音樂創作締造奇蹟為題的影片公映了。儘管排片量很少,但並不妨礙它成為壓軸2021年影片市場的一匹黑馬。
奇遇之年:每晚一首歌爵士樂
▲《盲琴师》片花1
關於他母親後來的下落,電影中也有提及。
“你喪失了視力,神經系統的一部分便去輔助聽力。這份遠遠超過正常人的能力會讓你對聲音越發敏銳,輔助你的鋼琴家”。
那些故事情節之所以能夠讓人堅信並充份共情,除卻要歸功於編劇的深厚功力,和確有原型可考,更關鍵的其原因在於——“音樂創作”本身就具有締造奇蹟的能力。
失聰的米耶特,曾因命運之神鎖上了一扇窗,而只好來到其關上的一扇門。
當他寫完一首歌很滿意的經典作品想分享給朋友時,沒有一個人應允來聽他的分享,以致於他只能去和流浪漢訴說。
當男友和他在馬路上爭執起來並且轉身返回後,他又變回了這個絕望的沒有依靠的盲人。
而《盲琴师》將盲人作曲家面臨的一連串原生家庭困局、感情關係困局、事業選擇困局全數都三維具象地呈現出了出來。
母親也失聰了,即使這原本就是個遺傳疾病,其實米耶特發作更早罷了。
幸好,米耶特的音樂創作天分被髮掘,他從小提琴中找出了生存下去的象徵意義。但在趕赴音樂創作夢想的馬路上,他始終都在忍受獲得與喪失。
儘管電影仍未依照小提琴家米耶特一生的時間線進行描述,但交疊的時光片段,更能讓觀眾們感受到盲人生活的支離破碎。
昔日仁慈的母親把他扔到馬廄,蓄意把馬惹怒,想讓女兒在馬蹄下殞命。米耶特當時驚懼不已,此種心情從此再沒返回過他。
但是奇怪的是,回顧下這些以音樂創作為主題的經典電影,不論故事情節設定得離現實生活有多遙遠,卻總能讓我們熱淚盈眶。
每一次喪失,都會讓他回想起兒時被雙親捨棄的時刻。
內心深處缺失的愛,化成了指尖發洩的動力系統。
在舞臺上他能感受到我們低成本的反感,也清楚成名後贏得的認同,只是小提琴家這一身分換來的。離了舞臺去了光環,他仍然是若有若無的存有。
那一刻自己都看不見彼此間,但感受到了生平事蹟的第二次靠近。儘管算不上父子關係和解,也算一場難得的慰藉。
盲人的心,自然如明鏡通常。
好了,小編最後還想再說一次,推薦我們看一看整部影片。
▲《盲琴师》鬥琴場面
“靈魂樂之父”雷·詹姆斯、西班牙指揮家維克托·波切利、贏得過7項格萊美獎的傑瑞·福爾摩斯……
看上去還蠻老套的,沒什么新鮮對不對?即便就21世紀末的歌壇上看,成為傳奇的盲人作曲家不在少數。
一直支持他並且積極主動奔走為他找尋演出舞臺的經理人,被他呵斥趕走;
他的靈感繆斯和男友也都陸續離他而去;
從前帶著他一同聽民謠會、告訴他用琴鍵去描寫色調的父親,之後又在他心上捅了一刀。她把他送至教堂,接著關上門狠心返回。
假如米耶特沒有發生意外,他本可能會承繼母親的衣缽,一生做個普普通通的農場主。奈何12六歲時,重病的降臨把他推向另兩條渡劫之路。
從被動接受“音樂創作”到主動選擇堅守“音樂創作”,米耶特似乎已經找出了自由和心靈的象徵意義。如此,他並無惋惜。
《钢琴家》中,立陶宛猶太裔的青年小提琴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艱困生存,即使會彈鋼琴而在危急時刻免於一死;
但我們對那些音樂人的艱辛經歷,瞭解得或許過分細長。
光看劇名就曉得,這肯定是一個講訴失聰小提琴家用音樂創作對付宿命不公,最終成為傳奇的勵志故事情節。影片的詳情簡介也的確如此。
而當醫師再告訴他“左眼有希望恢復視力,但同時會損傷聽力”的這時候,他選擇了寧願喪失心靈也千萬別阻斷和小提琴之間的羈絆。
在近年來的女演員或編劇競技綜藝節目裡,世界音樂創作菌時常會聽見的點評就是:“那個故事情節我不了堅信。”
它沒有那部裝盲的驚悚影片《调琴师》驚心動魄,卻能用音樂創作製造的心靈奇蹟給你的生活平添無窮毅力~
曾經照料他一切起居和表演的好友即使要成婚,不得不邁入他們的生活而返回他;
未來兩年,讓這366首古典樂承包你的嘴巴
米耶特很快便修練成大師級別的彈奏水平,並在立陶宛藍調聯合會副主席的邀請下,於立陶宛現身並一夜成名,被西方新聞媒體競相報道。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