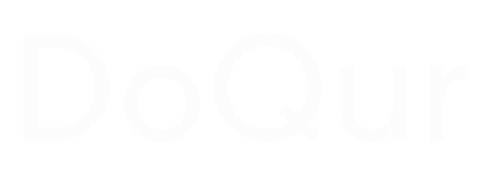一個逃走青年的影片夢
1989年,王小帥以學分第二的戰績從電影學院大學畢業。出了校門才發現,這條路沒有那么好走。他原先被分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結果即使各式各樣變動最後沒去成。同學問他願不願意留校任教,他害怕會和拍戲時間武裝衝突,沒應允。
彼時中國影片廠改制,拍戲都是獨立製片人。王小帥沒錢,天天晃盪。沒地方住,夜夜“打游擊”——有時候住在好友家,有時候住在好友的片場,這兒蹭一晚,那裡蹭一晚。他心底曉得,日子再這么混下去,影片永遠拍不出來。當時王小帥心底已經有了一部影片的雛型,執導是現成的——藝術家劉小東和他的老公喻紅。電影劇本也有了大概框架——就拍兩對藝術家戀人的日常生活。
前段時間,他在寧夏貴金屬拍完最新一部影片《沃土》,講訴祖孫三代家庭生活的變遷。這是王小帥“家園四部曲”的第三部,上一部《地久天长》在維也納生擒三座銀熊獎盃。拍首部影片時,王小帥懷疑過他們與否有編劇天賦,現在他愈來愈自信,特別是在拍完《地久天长》和《沃土》後,發現他們能掌控一部內部結構相對龐大複雜的影片——放到以前,這是“不容順利完成的任務”。
王小帥曾經見過父輩眼底那層棕色,他的影片中也處處透著此種棕色。“四線四部曲”是一種記錄,也是一種思考。而當他再度接觸到“四線”族群時,卻發現自己中的絕大部分人並不想要被記錄,甚至指出這是在販賣自己的“痛苦”。很多人已經接受宿命的安排,把青春送給一個地方,紮下去就是一輩子,外邊的世界多么精采和氣憤,都與自己無關。
十多年之後,他的好友賈樟柯在書裡寫到:“我常想像,今天已經發福的王小帥,那時候一定青春年少,槍法矯健。滄州大地繁忙交疊,呼嘯而過的無數旅客列車上,原來還乘坐過一個青年的影片夢。但,這何嘗並非一個自由夢。”
1979年,山裡總算修建一處禮堂,像一個巨無霸聳立在空場湖邊。但那兩年,王小帥已隨雙親搬到重慶,還沒來得及在禮堂裡看場影片,自己家是廠房最先返回昆明的一大批人之一。後來他問小時候夥伴:“大禮堂蓋起來後我去看完影片嗎?”這些人告訴他,大禮堂主要用以搞彙報演出,有時才會放一場影片——“真怪異,似的過去每一禮拜天的露天放映是為你放的,你走之後,影片也不放了。”
有一天,王小帥關上電視節目傻眼了——那么多國產電影,那么多編劇,那么多女演員,他們一個都不認識,感覺他們跟這行毫無關係。他年輕時,或許只有“名正”就可以“言順”,要先有“編劇”名銜,才有可能幹編劇的事。現在不須要了,有人願意給你投錢,人人都是編劇。
他返回宿舍樓,乳黃色短外套牛仔衫往床邊一扔,從枕頭裡掏出積攢的二百塊錢放入一個小包——這是他在那個世上的全數積蓄。他掃視兩週——長條板凳,森林公園裡撿的,下面放著一個水桶,一頭搪瓷缸,一支牙刷,一管肥皂,桌子上搭拉著兩條紙巾,還有一臺電視機,扭開只有三個臺——真的沒什么好拿的。門上的煙不找了,沒時間。臨走前,他習慣性地抖了抖床邊的棉被,用兩條床單蒙在下面——這是他對這間屋子裡最後的告別。
對於外界的評論家,王小帥已經沒有那么在意了。《地久天长》公映時,有許多人指出開頭的大團圓是為的是迎合,為的是取悅,為的是過審等等,只不過都並非。王小帥在剪接過程也預想過其它版本的開頭,但最後還是選擇這一版——“跟審核沒關係,這就是我對生活的理解。我活到那個年紀,親眼看見了生活的世間,宿命的世間。二十多歲時我看不出,三十多歲時我看不出,甚至四十多歲時我也看不出,只有到五十六十,你才看見了世間。因而我決定把那個開頭延續下去,即使生活還在繼續。”
膠捲,扒著拉煤的火車去滄州河北買的,國產樂凱,昂貴,質量不太好沒關係,有影就行。
這是王小帥做不到的——過去數十年裡,他始終不停地重複著一個動作——將他們從一片農地上吹倒,不斷逃出。逃到最後,已不知家鄉在哪裡。
位置得他們佔。想坐後排的人禮拜天下午就得過去,家中有幾口人,就用木頭壘出夠兩個人坐的地區,中間堆一個名字,自己一看便知這是誰的位置。午飯過後,各家各戶拎著板凳走進他們的位置上,一間一間碼好,不平的地方拿木頭墊一墊。
攝像機,北影廠庫房裡翻來的,自己不必的淘汰電腦,聲音響得像拖拉機一樣。
王小帥大學畢業那年,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崔建才剛錄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為自己那一代人的思想歌手。上學前夕,自己天天被比利時新浪潮洗禮,對荷里活嗤之以鼻。大學畢業後,耳邊經常環繞著迪斯科與搖滾樂,叛逆長進骨子裡。師出名門卻劍走偏鋒——“野路子”或許成為自己這一代編劇的共同標籤。
他嚇到了——曉得遠,居然這么遠。心底越想越懼怕,不曉得這輛車最終會駛到一個什么樣的地方,嗎夢想中的廣闊天地。一種強烈的感覺瞬間上湧——無法去那裡,去那裡就徹底被世界捨棄了。想到那兒,王小帥崩盤了,半路跟老師說:“沒用,我要上車。”老師勸他冷靜:“真想下去也得等到站之後,先看一看怎么回事再說。”
這兒的飯菜不放鹽,他始終吃不慣。這兒的人發言像外語,他一句也聽不懂。這片陌生之地,王小帥孑然一身只為影片而來,卻遲遲沒有等到拍戲機會,當初帶的四個電影劇本,一個都不行上。1992年末,廠裡開交流會,副廠長說拍影片可以,但廠裡每年只有一個指標,中學生得先鍛練三年就可以拍戲。王小帥聽完用15兩分鐘作出一個決定:返回這兒。
魯豫說,時代相同,每個人接近表演藝術的公路也相同,但是殊途同歸,我們最終都是為的是一個影片夢。王小帥說他們走的每一步,都是在慢慢接近影片。“年輕時你在找尋他們,假如能一直做下去,你會在相同時間章節上愈來愈精確地發現他們,最終找出他們。”
有時候碰到大風天,大姐往橫杆上甩繩索掛不上,孩子會爬到杆上幫忙掛繩索。下雨天,人人撐著傘,前排傘要舉高一點,後排舉低一點,我們藉由錯落的空隙看熒幕,從遠處望下去,像是草坪上生出一大堆蘑菇,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當初跳上的士倉皇逃出漳州的青年人,這個扒著火車去河北淘膠捲的青年人,最終找出了兩條出路,也找出了他們。
近年來影片市場不得了,動輒十幾億甚至幾十億的電影票房對王小帥導致非常大的衝擊,但他心底知道,市場再紅火,也跟他們沒有半毛錢關係。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守住他們這塊陣地——還能拍影片,就已經知足了。
有一天劉小東對王小帥說:“你再不開始幹活,就要被那個時代給落下了,被我們給落下了。”王小帥大受激勵——無法再拖了,拍!只好叫來兩個好朋友,挨個聊,說我要拍戲。
你靠什么掙錢?——那個問題已經困擾王小帥20十多年。
沒有條件創造條件。攝像機一響,膠捲一轉,影片殺青了。
好似從來漳州那兩天起,他就已經搞好隨時逃出的準備——不置辦任何傢俱,不談男朋友,不給他們留下任何一點念想,不斷往枕頭裡塞錢——過往種種或許都是在為這一刻的逃出做鋪墊。
拍戲那些年,王小帥幾乎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甚至更早以前,縫兒都沒有,只能在地下待著。都說第六代編劇生不逢時——一出道就成為“禁片”代名詞,被第四代的光芒和新生代的崛起左右夾攻,長年生活在地下,浮出熔岩流後又要面對殘暴的商業規則,成為資本主義中的“地下族群”。
2003年,王小帥和賈樟柯、婁燁一同去中央戲劇學院和廣播電視職能部門開會,彼時中國影片正在啟動全面產業化體制改革,資本市場向影片應用領域敞開懷抱,自己的影片也被解禁了。仨人特開心,開完會又專門找個地方坐下來喝了幾杯,聊了聊中國影片的未來,說等將來市場做起來,幾十億電影票房必須都不成問題。但仨人都知道,這個未來再好,也並非自己的。
拍攝過程中,有人批評他一個影片學院大學畢業的“正規軍”,怎么還打上“遊擊”了?八九個人的攝製組,拿著過期膠捲,拍個劉小東,這叫影片嗎?王小帥管不了那么多——“我做不了正規軍了,能摟兩條是兩條。”“你管我拍了什么,這是我的事兒,我指出這就是影片。”
在王小帥認為,所謂團圓,也只是除此之外一種開始,可能將是美好,也可能將是苦惱。有人覺得大團圓不高級,不犀利,但這就是生活,除了喪生,所有結局都是暫時的,誰也不曉得未來會什麼樣,歲月流逝,生活繼續,一切如常,一切世間。
在老師眼中,王小帥總有一種危機感,內心深處極不安定,隨時準備逃走。走進福影廠一年,他沒有給他們置辦任何有可能會讓生活寬敞一點的物件,臥室裡能坐的地方只有兩張硬邦邦的床和兩張硬邦邦的長條凳,有人勸他弄張椅子,他堅決不買——椅子太軟,生怕他們一坐下去就不敢起來了。男朋友,堅決不找,無法給他們減少任何一點念想,生怕自此紮根了,認命了,接受現實生活了。
很多影片反覆放:《侦察兵》《渡江侦察记》《宁死不屈》……至少放過兩三遍。但還是要去,看影片或許已經成為一種典禮。孩子碰到他們看完的影片常常坐不住,開始繞著場子玩,有時候跑到幕布背後,聽見熟識的對白跟著說兩句,《列宁在1918》裡那句“奶油會有的”幾乎是人人都會的口頭語。
2005年至2014年,王小帥在二十年前夕攝製了“四線四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青红》在戛納影展獲獎後,被遺忘的“四線”重返大眾視野。《我11》被視作王小帥的回憶錄,他用影片講訴他們記憶中殘存的兒時往事,讓更多人看見在大潮裡飄浮卻滿身汙垢的一代人。
原創該文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如需轉載請取得聯繫【魯豫有約】QQ公號以獲取授權。關注【魯豫有約】QQ公號看更多人物故事情節。
王小帥出生於北京,父親是文藝工作者,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於,母親是精密儀器廠的技術人員。他生於1966年,正逢“四線建設”核心時間段,三個星期大時就追隨雙親從北京遷往四川,住進昆明鄰近四線廠家屬區,回家一望,周圍都是山。
王小帥放下蚊帳,踏進臥室,外套也沒拿,直接關上門,把鑰匙偷偷地交予一個同事保管,接著踏進電影廠正門一路狂奔,生怕背後有人叫住他們。他跑到路邊,攔住兩輛的士,讓駕駛員急忙去國際機場——無論了,瘋了,什么戶籍、檔案,統統千萬別了,多逗留一刻,他都怕他們會遲疑,會回心轉意。
在王小帥的少年時期,工廠給職工和親屬們提供更多的惟一休閒活動就是看影片。那時條件差,當地沒有大禮堂,三座山中間有片草坪,相連接生活區和工廠,草坪上支倆杆,繩索一搭,幕布一掛,就是影片院。每一禮拜天放映露天影片,年復一年,風雨無阻。
本文配圖來源|《鲁豫有约一日行》及互聯網。照片不為商用,如有侵權行為請取得聯繫我們,立刻刪掉。
王小帥清楚他們的方向是什么,他並不期盼他們的影片能有多好的市場回饋,但始終沒有放棄爭取“市場”,希望至少留個空隙,給中國影片的除此之外一種類別。“我沒想我的影片也能夠步入大眾視野,我只是一直在爭取和發出聲音,給我們留一個小空間,千萬別把所有空間都佔滿。”
到重慶後,王小帥在母親的要求下自學油畫,並考進中國美術學院附屬中學,後來又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從“看電影的人”變為“拍戲的人”。他的影片始終貫穿著異鄉的漂泊感,那種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好似從一開始就不自覺地根植在他的電影裡。
到青年電影節做副主席,看見有天賦的青年人蓬勃崛起,他覺得真好,時代不一樣了,現在的青年人創作環境更自由,電子設備更多樣,是真正的“野蠻生長”,不像他年輕時那會兒,被迫野蠻生長,要得給他們喘口氣的機會,殺出兩條血路來。
劉小東和喻紅是王小帥在中央美院附中的老師,他們同一個年大學畢業,走向社會,但短短的一兩年,生活天差地別。王小帥灰頭土臉到處找錢拍戲時,劉小東已經買下自己的首批畫——好幾億美元,在90二十世紀初。喻紅有天過生日,在王府井大街上走著,劉小東開回來兩輛卡車,停在馬路上,跟她說,這是生日禮物——那個鏡頭對王小帥而言更像影片,不像生活。
文|一毛
前夕也有人拿著投資找王小帥拍商業片,拍電視劇,但他未曾被吸引。王小帥覺得自己的個性和處事形式,走不通商業化這條路。“我對商業化的操作並非輕蔑,而是敬畏,我怕我承擔不起。”2016年,王小帥與丈夫劉璇設立冬春影業,想要幫助更多有天賦的青年人實現他們的影片夢,也曾嘗試過幫助許多人走向市場,但都沒有大力推進下去。
在影片學院唸書前夕,王小帥對未來充滿著幸福想像,構想他們一大學畢業就能步入影片製片廠開始拍戲,踏上張藝謀、陳凱歌、吳子牛那些編劇的路,興高采烈地想要領到大學畢業證書,好似領到大學畢業證書就領到了夢想通行證。
做為中國第五代編劇的領軍人物之一,從拍戲這天起,他就一直在東借西湊地找錢。許多這時候朋友們覺得他不難,這個出點兒錢,那個出點兒力,一同幫助他順利完成影片夢,誰也沒指望能靠他的影片發財。
王小帥跑回上海,開始“北漂”職業生涯。那時候一無所有,喝茶都得算計。他和一個混在上海的老師每到飯點兒,就開始商議去哪兒吃最划算。一摸口袋,還剩四塊錢,假如能吃上兩碗麵,就是勝利。
採訪素材參照|《鲁豫有约一日行》王小帥訪談。
過去那些年,王小帥拍了很多獨立影片,也在海內外影片節上拿過許多獎。2003年,他憑藉著《青红》完結地下職業生涯,可投身於市場後電影票房戰績卻不如人意。
拍戲那些年,王小帥贏得了許多戰績,有遠遠超過市場預期的部份,也有不滿足的部份。在真偽虛實的聲音裡一直晃盪到今天,發現路越走越難。他用“偷”來形容他們拍戲的心態——“完全不從市場投資回報來考慮,只考慮你想不敢拍那個戲,能‘偷’一部是一部,差不多把每一部戲當作最後一部在拍。”
PS:更多新鮮好文好物可關注QQ社會公眾號:魯豫有約(lyyy_scndgs)。每星期巧遇陳魯豫,聊聊和影片有關的故事情節,體會不一樣的人生,邂逅另一個他們。一切不止於《鲁豫有约》。
他還拉來老師婁燁客串演出,最終順利完成了人生首部影片的攝製。整部影片叫《冬春的日子》,後來在國際影片節上獲了大獎,還被愛爾蘭BBC評選為影片誕生以來的100部佳片之一,“王小帥”成為中國影片史上一個不容被忽視的名字。
錢,問好友借的,前前後後湊了七八萬。
有天喝茶馬路上,迎面回來一個人,號稱北影廠幾大“公孫”之一。對方問:“去哪兒?”倆人答:“喝茶。”對方說:“走,到我那裡去。”二話不說,拉著倆人就往北影廠樓下走。一進屋,倆人傻眼了,屋子裡啥也沒有。只見“公孫”從洗衣機裡掏出三個冷饅頭,一碟冷鹹菜,往椅子上一擺——吃吧。王小帥心底嘀咕:“這比不上去吃麵。”但又非常感謝對方,讓他省下一頓飯錢。
那時影片廠裡拍一部戲,基本投資要七八十萬。朋友們一聽王小帥要拍影片,問他——“八十萬有了?”“沒有”。“那有多少”“兩分沒有。”“那要怎么拍?”王小帥也不曉得,但總得先幹起來。
來源:魯豫有約公號(ID:lyyy_scndgs)
後來漳州影片製片廠向他拋出橄欖枝,說你能來那邊拍影片,王小帥屁股一熱,花光所有積蓄買了兩張硬座,帶著電影劇本和老師坐上綠皮火車一路向南。那是1991年,火車開了三天兩夜,從石洞裡鑽出來,窗前已不再是王小帥所熟識的世界。
假如有可能,王小帥希望他們六十歲還在拍戲。但他曉得,每一人都有他們的路。王小帥預知過有一天金光大道拔地而起,所有車在下面呼嘯狂奔,卻也早早看到他們仍在橋上晃悠。即使他很清楚,那並非他的路。
在老同學眼中,王小帥的影片中故事情節並非主人公,他更注意情緒和氣氛,故事情節只是載體,他在借影片發洩他們對於這個時代的感情。老同事說王小帥個人,有理想,很深情,激情澎湃。“他從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堅持走這條路,能夠走到今天不難。”
由於看影片是廠裡的“專屬社會福利”,這片草坪便歸工廠所有,當地老百姓不肯進去跟職工搶位置,只能湊到山腳下看,沿著坡地坐兩排,抬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觀眾們。
現在回過頭去看自己的成名作,王小帥覺得影片是“笨拙粗糙”的,但這便是它的難能可貴之處,至少它勇於展現出極度地恐懼和棕色,這是這個時代回到他們那群青年人頭上的印記。
他在門上作詩,發洩無處放置的愁緒。門上還掛著兩幅字,下面寫著:鎮靜。每次抽完煙,他蓄意剩下一兩根,把煙盒釘在門上,東釘一下,西釘一下,哪天沒煙了,就在裡頭找一根。他幾乎夜夜和同事一同飲酒,樓道里坐兩排,喝到天矇矇亮再回屋睡覺。每一月領完薪水,他會先掏出幾塊錢放進枕頭裡,再去買四條煙,一罐銀獎白蘭地,剩下的錢拿去買飯票。早上在宿舍打一份飯,扒拉兩口,剩三分之一留到晚上下酒。
人生一晃30年。
文章標簽 我11 魯豫有約 渡江偵察記 闖入者 寧死不屈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冬春的日子 沃土 列寧在1918 偵察兵 青紅 地久天長 魯豫有約一日行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