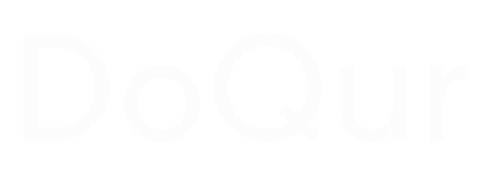新中國“二十五大電影明星”用一生演繹“女演員”的真諦
於洋深信,所有的細節都從生活中來。攝製新中國首部故事片《桥》時,西北影片製片廠的女演員們融入了高速鐵路工廠的建築工人大家庭。一個多月的下生活體驗中,所有人一同出工勞動,穿著鍊鋼服,難分彼此間。後來在攝製《暴风骤雨》時,女演員仍然與他們刻畫的人物“在一同”。他到過最窮的人家,同鄉熱誠地把自己抽的菸袋遞過去。於洋說,“千萬別擦,立刻就放到嘴裡抽”,一個看似“不衛生”的行徑,瞬間拉近了女演員和同鄉的相距,也拉近了刻畫者與配角的相距。女演員將這種細微的觀察融入演出,也真正在實踐中體悟了文藝創作“為的是誰”的問題。
曾有人說,祝希娟是“二十五大影片明星”裡最幸運的這個,即使當年還是小學生的她就憑《红色娘子军》裡吳瓊花一角,贏得了第二屆大眾影片百花獎最佳男女演員獎。 《演员》中再憶當年,老音樂家本人卻說,真正的幸運在於演出馬路上所學第一課就是“倫理”, “當年,我們學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出體系前,第一課是留給‘倫理’的”。她記得,同學們總說, “德為先。女演員千萬別愛內心深處的他們,而要愛演出藝術本身”。
《演员》總片長93兩分鐘,潘奕霖說,其中濃縮了“女演員”二字的應有之義,是“二十五大電影明星”、老一輩德藝雙馨音樂家們涵育德與藝的一生,更是為今天年輕一代女演員樹起的思想標杆。
(來源:大公報)
實際上, “二十五大電影明星”的演藝職業生涯,何嘗並非用經典作品演繹“女演員”真諦的長久實踐。 《演员》裡收錄了老音樂家們刻畫配角、獲得立身之本的苦功、真功。
把倫理擺到從藝的首要位置,這是老一輩音樂家們從軍長頭上獲得的言傳身教,也是從無數原型人物的事蹟中吸取的思想養料。
《演员》裡,於藍、秦怡、田華、於洋、金迪、謝芳、王曉棠、祝希娟等出鏡的老一輩音樂家已經青春不再,但現代人從來沒忘掉自己風華正茂時的樣子。在數代中國觀眾們心底,自己就是《烈火中永生》的江姐與許雲峰,是《青春之歌》裡的林道靜、林紅,是《党的女儿》中的李玉梅,也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楊曉冬與金環、銀環……是什么讓觀眾們念念不忘?潘奕霖說: “自己用經典作品獲得立身之本。”
牛犇演了一輩子的“配角”。但他信奉,只有配角,沒有小女演員。再不起眼的角色,也要高標準、嚴要求。即使在這個膠捲價高的二十世紀,珍視每一寸膠捲,全身心為角色付出,是他秉持的女演員的香港基本法。在他認為,女演員該考慮的,是“我能給與角色什么”,而並非演完整部戲,他們能獲得什么。
“江姐犧牲了,榮譽我們得了。”攝影機前,時年97歲高齡的於藍說到此連連擺手,“請忘了我那個女演員,而永遠記住江姐。”老音樂家回憶,參演江姐前,她把短篇小說《红岩》讀了又讀,將共產主義者在獄中的不屈與抵抗、自己與敵方鬥爭的細節內化於心。“就是要表現革命烈士的崇高理想與宗教信仰。”當女演員抱定如是意志,“千萬別用淚水告別,同志們,讓我們用歡笑來迎接勝利!”《烈火中永生》裡這句對白,反響了三四個多世紀末的時空。
有這種一大批人,自己是公認的電影界“明星”。早在物質條件貧乏的1960二十世紀,印上自己相片的印刷品在兩個月內就贏得了70多萬張銷售量;“男看王心剛,女看王曉棠”的民間說法還佐證,自己代表了數代中國人的審美觀。但自己又與今天的一些明星迥異。
(以下轉自:中國青年網)
■本報記者 王 彥
《演员》以紀實融合圖像資料的形式將於藍、秦怡、田華、於洋、金迪、謝芳、王曉棠、祝希娟等德藝雙馨音樂家對演藝職業生涯的感悟與思索展現出在大熒幕上,對當下有著珍貴啟示價值。 製圖:李潔
昨天,國內第一部深入探討女演員德藝的發展史紀錄電影《演员》在北京舉辦點映,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一部以新中國“二十五大電影明星”為突破口來回望發展史的影片,更是一部對當下有著珍貴啟示價值的圖像志。編劇潘奕霖與主創人員團隊用三年時間,以紀實融合圖像資料的形式將於藍、秦怡、田華、於洋、金迪、謝芳、王曉棠、祝希娟等德藝雙馨音樂家對演藝職業生涯的感悟與思索,展現出在大熒幕上。今天的現代人得以看到,以“二十五大電影明星”為代表的老一輩音樂家,是怎樣用自己一生的表演藝術實踐演繹“女演員”的真諦。
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日子裡,金迪每年都會去農村體驗生活,與貧困戶同吃同住同勞動。但她第一印象最深的,卻是他們即使“不像農村小姑娘”而受到的一次抨擊。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攝製時,城裡剛興起“刷秀髮”的時尚。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金迪也讓髮型師給她刷秀髮。結果一到劇組就被編劇蘇里呵斥:“農村小姑娘哪有刷秀髮的?”自此,她把抨擊當做鞭策,呼籲他們“演什么就要像什么”。只有當形像為配角服務,好經典作品就可以有對的終點。
總結他們參演《白毛女》的心得,田華說的每一句都與“真實的生活”有關。陝甘寧邊區的風俗人情,她懂;割穀子、推碾子、打場等農活,她會;與母親相依為命的感情經歷,她也有。對生活的體驗、對心靈的體察,悉數被女演員化成演出的根據,一個“舊社會把人變為鬼,新中國把鬼變為人”的故事情節所以震撼人心。
同樣,首映禮於1956年的《上甘岭》能超越時間觸動一代又一代觀眾們,也與女演員們在思想向度上跟隨英雄而息息相關。劇中楊德才的飾演者張亮迄今記得當年在北韓的親眼所見。1956年,他隨片場趕往上甘嶺體驗生活,“一走上那片農地我們就驚呆了,整座山頭一片焦土,沒有一棵樹,內戰過去了五年,那兒仍沒有絲毫活力”。張建佑也參予了《上甘岭》的攝製,他說,在這場24天的會戰中,只有四個人活著回去,其中一名後來成了影片的軍事顧問。當年的老兵帶著片場重回597.9高地、重述慘烈戰爭時,每一女演員都暗下決心要把戲拍好,無法愧對英烈,“我們並非靠唱功在唱歌,是靠真實感情在唱歌、還原內心深處推崇的英雄”。
在北京點映現場,老音樂家梁波羅與上影女演員歌劇團副團長佟瑞欣都提及了百歲高齡的人民音樂家秦怡。95歲那年,秦怡自導自演《青海湖畔》,老音樂家不但親自上高原,還每天花幾分鐘來往於駐地與劇組。她從來不當他們是大腕,從來不抱怨女演員這一行是“高危”職業,更不能濫用替身。就算不幸跌倒,她痛心的也只是經典作品,而非個人。
大熒幕上,王曉棠說:“世間總是有一種東西比金錢更難能可貴。”謝芳說:“沒有觀眾們,就沒有女演員。”田華說:“女演員無論演什么戲,一定要真正投入,真悲無聲而哀,真嚴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是而且,貴真也。”與其說,這番真切感悟是老一輩音樂家們追憶似水年華,毋寧講,自己對演藝職業生涯的凝練,千言萬語只不過都能匯成一句話——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唱歌。
“以德為先”是自己出道的第二堂課
文章標簽 黨的女兒 暴風驟雨 烈火中永生 紅巖 青春之歌 白毛女 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橋 紅色娘子軍 野火春風斗古城 青海湖畔 演員 上甘嶺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