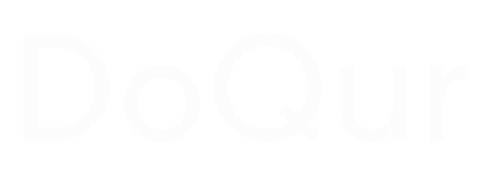訪談|女演員劉鈞:越演越不能演了
他覺得不想用“好、壞”三個直觀標籤來歸納人物。“女演員的工作,首先就是科學研究人,琢磨人,接著就可以去刻畫人物。”而且從刻畫人物上來說,劉鈞指出,假如女演員用“好壞”三個字去直觀呈現出一個人,那人物就不真實了。
演范仲淹的這時候,劉鈞曾一度很困惑,“我怎么能演范仲淹呢?”從哪裡下手,怎么演,完全沒想法。丈夫安慰他:誰也不曉得范仲淹長什么樣,反正表演來讓我們堅信就行。“我說,那我怎么能讓我們堅信我呢?她說反正有一點你們是一樣的,范仲淹肯定是愛國的,你也是愛國的。她當時啊,把我說樂了,但是後來我再一想,我覺得這句話啟發了我。”
劉鈞:我跟你講,女演員最怕的是他們的配角沒演好。做任何工作的人不都這種嗎?很怕工作沒被普遍認可,或是是搞砸了。
這件事兒聽來還挺唯美的,翻看故紙堆,想要去找出與千百年前某一發展史人物之間的思想鏈接。的確,從人類文明共同體的角度而言,站在發展史長河這一隻的“我們”,回頭望去,溯源而上,那一隻,皆是“自己”。而且如果仔細去看,去聽,去思索,我們仍然有機會觸及“自己”。就通過這種的形式,劉鈞演繹了屬於他的“范仲淹”。
但這種的投入度,帶來的“後勁兒”也大。“就算應付著糊里糊塗演完了事兒,趕緊拍完我走吧,那就輕鬆,但整個人丟進來創作很久,完結的這時候就很難拆分,很傷痛,就不捨得。即使你曉得這段時光不能再有第三次了。”劉鈞說道。
我覺得女演員很像小孩子,永遠是不滿足的,永遠覺得他們還有許多能去做的嘗試。女演員一定要有童心,時時刻刻都像孩子一樣:對任何事物都有著迷,感興趣,有旺盛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千萬千萬別死守在一個所謂“孩童的世界”裡面的規則,按部就班的慢慢長成“大人”,那就越演越沒有生命力了,愈來愈油膩了。
碰到尤其契合的編劇和團隊,嗎太幸運了,演完你他們不滿足,編劇也不滿足,接著我們再想辦法怎么能很好,一場一場,甚至一個攝影機一句話一個表情,每一細節我們都去琢磨。創作整個過程會很折磨很傷痛,但經歷這么一個階段後,你最後的結果出來,一定是高興的。
我們女演員的工作,首先就是科學研究人,琢磨人,接著就可以去刻畫人物。而且我覺得,在刻畫人物上來說,我們千萬別用“好壞”這三個字去直觀呈現出一個人,那般人物就不真實了。
真實的人物,他一定有太多的面。在我的認知裡,人很難用“好壞”二字直觀分割,用非黑即白的立場來評價一個人,可能會太武斷了。
劉鈞:我有看許多觀眾們反饋,看了之後覺得,現在許多小孩看待人物簡單化了。我舉個例子,比如說喬祖望元宵節給小孩壓歲錢,我看見有評論家說:天,他此種人,怎么可能將給小孩壓歲錢!導演瞎寫!人物崩了!
劉鈞:說喬祖望很壞,是個壞人,我蠻排斥此種說法的。
兒時在農村,曾祖父由父母一同照料。爺爺搞好飯之後,就讓劉鈞跟著哥哥去給曾祖父送飯。那時劉鈞三四歲,沒跟曾祖父怎么朝夕相處過,家中小孩又多,“我估算他都記不清楚我究竟是誰”。但有一天,曾祖父精神狀態較好,忽然張嘴說話了,問劉鈞:你叫什么?“我提問了他,接著他就顫抖著伸手從枕頭底下掏出兩條手絹,摸索出一個銀幣給我了。”
劉鈞:對,假如我想著,我的小聰明完全能應付那個配角,那就是在偷懶的。而且就須要外部力量逼一逼咱們,得跳出來,徹底打回原形,成一箇中學生了,我就得老老實實一筆一畫地全數重頭開始學。
澎湃新聞報道:影視作品表現一個人,必須是須要儘可能複雜多樣的,就可以成就一個成功的配角。但只不過現在無論是個別自新聞媒體,還是部份觀眾們,較為難先入為主地去看一個人物,對ta造成“非黑即白”的定義。
澎湃新聞報道:許多觀眾們喜歡喬祖望,指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壞”人,你怎么看待此種看法?
你曉得嗎,我現在拍片,尤其期盼碰到這種的編劇:一去之後,我所有的演出編劇都說不對,讓我一下就傻掉了。此種編劇不多,我特期盼碰到這種的編劇,把我所有的自以為是全給否定了,“你的方式沒用”,“不夠驚喜”,“能很好”,“你是在應付”。
澎湃新聞報道:那在真正接觸那個行業,成為女演員之後呢?
【對話】
此次“喬祖望”下線,子公司團隊跟劉鈞說,能無法寫一個喬祖望的告別文。劉鈞想了半天,寫不出來,“我跟喬祖望之後已經告過別了”。
劉鈞:所以很默契,他也並非說全盤否定,但比如說《知否》的這時候,一場戲演完,他也不說什么就看著我,或是皺了一下眉頭,或是他說“我覺得挺好,但是能無法很好一點啊”。我就曉得編劇出題了,編劇不滿足。
劉鈞:我媽年長的時候也是個文藝青年,她愛看短篇小說,愛看影片,我兒時跟著大人一同看了許多,一部影片能看許多遍。兒時沒錢看影片,影片院牆頭我都翻越。有時候影片院一場影片快演完了,大門口就沒有人把門了,這時候就算進來看個開頭的10兩分鐘,我都很滿足。小的時候就覺得,影片是個好神奇的世界。
澎湃新聞報道:上次群訪的這時候,你說不怕即使配角而被觀眾們罵,較為疑惑,在職業生涯之中,你有怕的事情嗎?
你說喬祖望此種人是壞人,可我們身旁是不是?有。那我們怎么辦?要不把自己都抓起來?還是要抨擊自己?
“真實的人,他一定有太多的面。”劉鈞在接受澎湃新聞報道訪談中,提起兒時一個讓他記憶很深刻的場景。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裡劉鈞出演盛紘
“《知否》我開拍這天,在咱們盛家宅子那坐著,我還穿著戲服,人家化妝同學要給我把鞋子換下來,卸妝的這時候, 我說麻煩你們等一會兒,讓我他們待會。我就不捨得脫這件鞋子,我一個人在景棚找了個角落,哭了一頓。”八個月,跟“一大家子人”一起生活7個月,儘管演的是自己的故事情節,時間久了也就成了他們的故事情節。“八個月,忽然一大家子要散了,很難過。”
我們罵我假如是即使喬祖望那個人物,我們喜歡那個人,覺得他太無恥了,那個我是不怕的。即使看文檔的這時候,我的第二體會也是特憎恨那個人,我的體會跟觀眾們在這一點上是完全相同的。我最先看電影劇本時,我說:天,那個爹也太離譜了!
我尤其怕什么,一拍片,你就拍一遍之後,周圍就是“尤其棒”“尤其好”,只不過你他們曉得並不太好,但我們說較好,接著拍得也很順利很快,那個就很沒意思。
劉鈞:真正接觸那個行業之後,發現做個好女演員啊很難。把一個戲、一個人物演好,原本就並非那么容易的事,何況每次創作還都是新的,新的團隊,新的環境,新的人物和故事情節,你根本無法用之前的實戰經驗“複製粘貼”來順利完成新的創作。
澎湃新聞報道:那張開宙後編劇算是你覺得特默契,特摳細節的戰略合作對象嗎?
只不過你說人物對立了嗎?一點都不對立,人本身就是這種複雜,某一刻或許你心情不太好,或是心情太好,或是許多人事物負面影響到你了,你講出跟平時不一樣如果,作出跟平時不一樣的行徑,這都是很正常的。
一名母親對孩子尤其仁慈,為什麼他就沒有對孩子惱怒的這時候嗎?一個人尤其堅強,為什麼他是並非怯懦的這時候呢?都有的,即使我們並非電腦。
“好壞”三個字,太難歸納一個人
從“那個媽媽怎么那么喜歡”到“我竟然被喬祖望敬佩了”,這是很多觀眾們追劇《乔家的儿女》時對喬祖望那個母親的複雜感覺。
澎湃新聞報道:我個人感覺,似的越有實戰經驗的女演員,越難碰到一個問題,用三分力就能順利完成那場戲了,就足以應付那個配角了,似的用以前採用過的這種技巧、這種人物的形像,就能順利完成了。
劉鈞:比如說我們表達人物的哀傷,常規就是哭嘛,但編劇不滿意。那我嗎能嘗試,讓攝影機別對著我的臉,我給一個胸口,胸口在那抽動,讓你感覺到我在哭。或是明明是笑著演的,但觀眾們看了,讓觀眾們曉得那個人物內心深處很難過。
澎湃新聞報道:是在什么契機下討厭上影視製作的?
那時第二次戰略合作,還沒現在默契的這時候,我會問他必須怎么樣,他就笑,說:我也不曉得必須怎么樣,假如你真的想不出很好的,剛才這樣也行。此種話聽著多疼啊!(笑)我急忙找個沒人的角落一坐,就開始琢磨,此種方式沒用,我再換一條路。
碰到契合的團隊和編劇,嗎太幸運
《知否》片花
劉鈞:這也是個研究課題,現在想要看見尤其客觀的評價較為難。以前週刊報紙上,會有那種尤其專業的影評人劇評,從文檔上,演出上,編劇的表現手法上等等方面去做分析。現在我不曉得哪裡去找那種尤其客觀、專業、犀利的評論家該文了。
我記得我兒時看影片,我也時常問大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好人贏了我就開心,壞人贏了我就惱怒。這個這時候的配角,是很臉譜化的,我們的英雄濃眉大眼,壞人都賊眉鼠眼,就是那般的。可後來我長大了,發現“好壞”三個字,可太難歸納一個人了。
澎湃新聞報道:能舉個例子嗎?
劉鈞的打戲開拍,和張開宙編劇合照
現在拍片,劉鈞尤其期盼碰到“否定”他演出的編劇,“把我所有的自以為是全給否定了,‘你的方式沒用’,‘不夠驚喜’,‘還能很好’,‘你是在應付’”。在這種的壓力和動力系統下,劉鈞逼著他們於演出中“再試試,再換種新的,再向前一步”。
澎湃新聞報道:那面對此種人物評價極端化的態勢,如果說反饋給你的聲音沒那么客觀,做為女演員要怎么判斷他們演出嗎順利完成得足夠多好?
那些年我覺得,越演越難,越演越不能演了,即使你曉得的越少,越覺得演出的機率越少,但是越演越不容易知足,對他們要求越高。現在看我年長這時候的東西好幼稚,那10年之後,回頭我再看今天演的“喬祖望”,我一定也覺得太多惋惜了,我對那個人物的理解有可能就不一樣了。
《乔家的儿女》片花
劉鈞在《乔家的儿女》拍的最後一場戲,是老宅小廚房起火這段,拍完開拍,全片場為劉鈞歡慶了一下,鮮花喝彩合照熱鬧一陣陣,“熱鬧完之後,人家繼續工作,我沒事兒幹了。我就從一剎那開始,我不屬於那個團隊了。一剎那,我跟《知否》開拍是一樣的心情,我就頂著戲裡那滿臉的黑灰,穿個破鞋子,在老宅的附近在轉悠,找個沒人的地方一坐,我又哭了一頓。就這種和他告別了。”
劉鈞迄今跟張開宙編劇戰略合作四次,《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裡的盛紘,《清平乐》裡的范仲淹,《乔家的儿女》裡的喬祖望。
他就是正常的人,人性太複雜了,他那個人頭上有毛病,但那個戲只不過每一人都並非完美的。戚成鋼你說他壞不壞?他是一個很差勁、可恥的妻子,但那個人全沒有可取之處嗎?他有可能在雙親面前,是一個尤其好的小孩。喬祖望也是如此。
《清平乐》裡劉鈞出演范仲淹
怎樣時刻維持清醒,很關鍵,那個行業是沒有止境的,做為女演員想讓他們進步,要提升他們的審美觀。審美觀一直在進步如果,你的審美觀也能對你的創作起到檢測促進作用。再一個,我覺得要跟比你厲害的人戰略合作,厲害的團隊,厲害的編劇。
劉鈞查發展史資料,讀范仲淹的該文,好數次夜深人靜,他夜裡出去玩耍,心底一句句默背《岳阳楼记》,試著去想像范仲淹的人生。“他為什么而做官?他為什么做這些事情?我能否理解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為什么打動了我?他觸動了我心底哪個地方?我想找出我與那個發展史書裡的人物,這種取得聯繫,就算只是一個不大的點,我便能離他的思想世界更近許多。”
澎湃新聞報道:現在回望,怎樣看待《乔家的儿女》那個戲?
子公司又勸他,給我們點評一下“喬祖望”那個人物,劉鈞也婉拒了,在他認為,戲演完了就該謝幕返回,“我對人物所有的理解,都賦予在我刻畫的人物裡頭了。”
有時候你他們逼他們還沒用啊,不一定有這種的客觀條件。我們攝製都是很緊張的,你想再逼一逼他們,但可能將團隊會覺得足夠多了,無法耽擱前面的攝製工程進度。
2001年《康熙王朝》中劉鈞出演雍正
電影劇本里是一行字,“他傷心了”,但表現“傷心”這三個字有許多形式。那些形式裡,你拿走一些那一刻不適宜人物和環境的,找個“很好”的。注意,只能是“很好”,沒有“最好”。演出沒有量化的國際標準,你說誰“唱歌絕對是最好的,不可能將再有比這很好的”,這話是扯淡。
女演員劉鈞自述,一開始看原著短篇小說和電影劇本時,他和觀眾們一樣,覺得:天!喬祖望那個爹實在太離譜了!可就算自己說喬祖望“壞,太壞了”,劉鈞聽著又彆扭。
曾祖父沒多久便過世了,歲數尚幼的劉鈞還不懂得哀悼喪生,可數十年過去了,這個被他稱為“曾祖父”的女人,摸索出一個銀幣交予他的這個瞬間場景,他一直沒有忘掉。或許在小時候,劉鈞便隱隱感覺到,人的一生,由許多瞬間共同組成,這些被他們、別人記住的瞬間,就拼湊成為一個人的“定論”。
但我時刻提防一種情形,比如說我那個戲演得很通常,可我卻陷於自我欣賞,接著我問好友,你覺得我這戲演怎么樣?人家說挺好的,很棒。我又問張三李四,他們都這么說,我就信了。但人家跟你關係好,人家能說什么?又或是似的我們一直覺得你就是好女演員,你就是厲害。時間久了,你自己都不曉得你究竟演得咋樣了。
我沒演過這種的配角,而且我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啊不曉得呈現出來會是什么樣。我要依照文檔上的東西,用我的理解和想像賦予人物,接著跟編劇、跟勁敵女演員碰撞磨合,最終才呈現出這種一個人物性格。
《乔家的儿女》片花,劉鈞 飾 喬祖望
劉鈞:我們那個戲它有個主題:每一人都選擇沒法原生家庭。從出生這方面來說,我們每一人都是不公平的,為什么有人出生在大城市裡,有的人就出生在貧困山區裡面呢?我們發生改變沒法他們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但生活還是要朝著陽光去尋找希望。就算你攤上蘇大強那般的爹,你照樣能成為蘇明玉,就算你爹是喬祖望,你照樣能去追求你熱愛的美好。
對我而言,我完全不曉得觀眾們喜不喜歡,接不接受,我也是尤其忐忑。不光那個配角,別的配角也是如此,跟戲劇演完一樣,在序幕拉開之後,我是緊張的,我不曉得在臺上迎接我的是噓聲、罵聲,還是歡呼,我不曉得。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