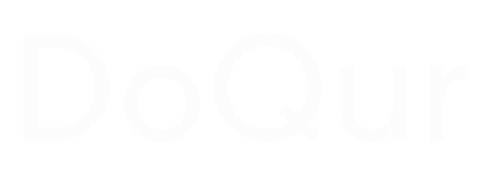當留學生決定歸國做影片
“以前聽見許多曲目或是故事情節,腦子裡就會形成鏡頭,想把它拍下來,聽覺化。”何遜說當時的老闆娘指出他審美觀很差,他為此看了很多電影,在“補課”的過程裡,他看了許多經典的影片,為圖像的氣質著迷,辭了工作,去英國電影學院自學攝影。
在國外的這時候,何遜更多的是和好友一同拍小學生作業或是大學畢業經典作品,華裔在國外有詞彙和人文的障礙,很難在英國的主流圈子裡拍東西,青年人多半是拍許多邊角料,或是隻有財政預算非常有限的電視廣告片場為的是省錢,才會找華裔攝製。
青年電影節、創投和各式各樣青年編劇扶植計劃,是現在的青年人能看見的最公開、公正的機會。此外,新人想要步入長片的攝製始終有較為高的准入門檻。
“我曉得這兩條線是武裝衝突的。”劉天力在想,能無法在認同爸爸媽媽的意願和做編劇這兩件事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儘管現階段還沒有找出答案,但有一點還是明晰的:現在我28歲,希望能在35歲之後,拍出我的第二個長片,僅此而已。
當年長的血漿源源不斷地湧向一個略顯疲態的行業,也許會帶來許多潛移默化的發生改變。
相同的影片基礎教育體系,對影片人的培育形式和要求也相同。在英國影片學院學藝術設計,經常會被丟進許多情景裡:藝術甚至會模擬和編劇複試,在一個隨機的電影劇本里,兩方做準備,接著溝通交流,而導師會在其中給出具體細微的建議。
通過校招,她進了華誼兄弟的項目部,編劇是她想一直從事的職業。在英國南加州大學的布萊恩·艾華萊士與理查德·楊表演藝術、技術與商業技術創新學院,她學的是表演藝術信息技術與商業技術創新專業,要學設計、動畫影片和電腦程式設計、資料庫等等,“聽起來似的和影片沒什么關係”。
而歸國後,比做影片這件事擺得更靠前的,是怎樣生存的問題。何遜形容他在北京的工作是“恰飯”。回去後他拍了一部網劇,發現對攝影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把編劇想要的鏡頭拍出來,攝影他們的創意設計輸入非常有限,“在英國的基礎教育體系下,我以為攝影是從電影劇本故事情節階段就開始介入的。”
何遜專科階段的自學幾乎和影片毫不相干,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學院的物理學和科技專業大學畢業後,他去了一間製片子公司,給子公司做頁面。工作的過程裡瞭解了一個劇組的配置,在編劇、攝影、藝術等相同的工種裡,他醒來一直對攝影很有興趣。
行業准入門檻也始終存有,青年人步入的渠道並算不上暢通,帶著經典作品出席影展、走創投,去影視製作子公司下班,又或是是花大把時間精力“認識人”、靠後輩提攜,無論何種選擇,都是兩條漫長的公路,而且許多從業者揶揄他們“二十歲了依然青年電影人”。
毒眸與包含編劇、製片人、攝影和藝術在內的5位海歸影片人聊了聊,企圖去探討在禽流感之下,影片市場遭遇非常大的衝擊,行業的革新正在醞釀之中,此種情況下,帶著影片夢歸國的青年人,必須怎樣來到中國影片市場、與之共同摸索出成長的方向和路徑。
張蒲中天在國內讀專科時,第二次進片場,學的第一件事是搭鋼架、搭高臺,也幫我們訂房間、訂飯、搬東西收雜物,“說是接觸製片專業,只不過也是小場務。”他覺得一直做執行有瓶頸,要想深入瞭解影片創作的各個環節,成為一個符合要求的編劇,還須要在現代文學、表演藝術層面多樣一下他們,就去了白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讀研,學的卻是表演藝術評論家-蘇俄影片方法論科學研究方向。
不止於此,社交、人脈關係和資源,是許多青年人步入影片行業、贏得機會的關鍵渠道。何遜沒有采用過QQ朋友圈的機能,他覺得他們不討厭也不擅於社交,“我認識的人不多,在國外能收到的工程項目都不多,剛歸國就更不用說了。”
“留學生必須有錢吧,拍影片還要眾籌?”
王鈺媛現在做為子公司的編劇之一,接觸了好許多類別的電影劇本工程項目,驚悚、奇幻、青春、動畫電影等等,但要找出一個好的故事情節,順利完成研發、攝製,最後公映、看見觀眾們,王鈺媛覺得這是一段很漫長的路。
一開始只是給拍影片的老師、好友幫幫忙,或是在片場訂餐、買水、搬搬東西,“甚至連生活製片人都算不上,就是一個場務。”王鈺媛說。但在幼兒園上了一節制片人課外,大致瞭解了荷里活工業體系下製片人的程序,她發現“製片人居然是一個這么體系化、模式化、有科技含量的事”。
相比之下,已經是職場人的王鈺媛,儘管參予子公司的工程項目還沒有正式啟動、攝製,但工作依然讓她處於一種充滿著期望的狀態裡。她想起小學生時代拍戲,一個關於同性題材的影片,眾籌到了5萬塊錢。即使許多人對於留小學生回去拍戲、籌錢這件事的立場都是:既然你有錢出國上學,為什么還省著幾萬塊錢來眾籌?
“製造許多情況,讓我們去思索怎么辦,只不過會發現藝術並並非只學好他們的專業,片場各個工作崗位的工作都須要我們瞭解。”趙依銘說。
劉天力則發現許多年長的編劇即使種種不利因素負面影響,不太敢去觸碰一些社會話題,很多人都在聊他們的內心深處和身旁的一些小事,他覺得拍戲的人還是要有一些擔當:“儘管我們難以像袁隆平後輩那般,作出造福人類的偉大重大貢獻,但至少我們能做一個人文傳播者,關注、記錄我們生活的社會和時代。”
劉天力最近正在好友的劇組裡幫忙,即便是做打板、場務的活,也覺得很高興。他討厭為的是拍戲跑來跑去的感覺,或是是在家寫影片劇本、聊中後期、和團隊的成員爭執,都能找出“每晚都在技術創新”的象徵意義;如果有與做影片有關的工作,他都願意去做,“拍互聯網影片也可以,如果有機會也可以拍得較好,能做編劇,或是能呆在片場我就很滿足了。”
關於是回到國外還是歸國,劉天力和他在英國的老師“吵了”很多年,他屬於堅定地看好國內影片市場的那一派。歸國後他去了一間幼兒攝影子公司,做抖音短視頻,他們對影片的理解到了那兒似的完全不適用了,幹了一個月後辭了職。
編輯 | 趙普通
何遜到月底就30歲了,而他的中長期目標是30歲之後拍一副部長片,“沒用就往後推一推,31歲。”他笑說。
劇組,還是職場
每年都有數百名像劉天力這種的青年人決定歸國做影片。自己遊學十多年、接受了專業的影片基礎教育,但國內的影片市場對自己而言,有時候是陌生而遙遠的:錯失了中國影片市場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兩年,對行業的瞭解也相對貧乏,自己的人脈關係和資源更是少之又少。
王鈺媛是四個歸國的青年電影人裡,現階段惟一有“正式工作”的。
文 | 張穎
當年與劉天力“辯論”、堅持要在國外做影片的老師,自己指出“國外有影片工會組織,許多合法權益會獲得保障。但是很多人回到國外多半是做中後期、剪接和聲音等,劉天力覺得編劇此種創作型的工作,返回中國的沉積物,創作的東西會非常表面。
“而且能籌到錢還是挺憤慨的,沒有想到那么多人支持我們那些青年人。”王鈺媛說。
“他們對於細節的控制是我之後沒碰到過的,讓我覺得影片製作、幕後的工作太有氣質了。”趙依銘決定選擇藝術、服飾方向,去英國影片學院讀了藝術設計的本科生,“這是我討厭的東西,想精進一下自己。”
而即便有片子可拍,能從中贏得的投資回報,也常常和錢沒有關係。張蒲中天歸國後去華語青年電影周工作了一兩年,認識了青年編劇艾麥提,做為艾麥提的製片人,順利完成了影片《手风琴》。“沒有錢賺,為愛電力,但我們現在拍戲也並非為的是掙錢,還是要多積累實戰經驗。”他說。
現在已經有趙依銘在英國唸書前夕的老師,拿著創作的影片工程項目進了創投,這讓她覺得很高興:自己的經典作品漸漸成形,似的我們這一代開始步入國內市場了,能被大家看見這件事,想想就很興奮。
而對於他們想做的東西,影片、電視劇或是電視廣告都能,在趙依銘的構想裡,要用一輩子的時間,去做一個好的藝術指導,“重點在於做他們討厭的故事情節和類別,我覺得精力有限,不敢耗用在沒有激情的事情上。”
劉天力在甘南草原編劇《风行草偃》
有多名資深從業者對毒眸則表示,青年人沒有長片的攝製實戰經驗,即便有較為傑出的影片、MV經典作品,自己也“不肯用”;成熟編劇身旁常常都有固定的戰略合作班底,而新人步入片場,多半是從助理開始:“之後也用過海歸,對於在現場拍拍空鏡、換換攝影機那些瑣碎的事情,許多人覺得浪費了自己的專業,無法接受。”
不止於此,國外攝製和中後期有嚴苛的時間控制,而歸國後大家似乎習慣了犧牲個人的休息時間去順利完成工作——趙依銘希望在那個與行業碰撞的過程裡,當青年一代的電影人有定價權時,能讓此種情形出現許多變化,“比如說工作時長、勞動安全保障等問題,也許須要我們那些在國外學過相對健全的工業體系的人去一點點發生改變。”
《手风琴》開拍照
行業裡有兩個編劇後輩是他的歌手,他希望他們在到了“歌手”的歲數時,也能有拿得出手的經典作品:“現在還年長,可以專注於怎樣成長為一個傑出的編劇那個問題,歲數再大一點還沒用如果,我就回來放羊。”
劉天力居然,在28歲這年,他們的信息會被爸爸媽媽列印出來,掛到人民森林公園的相親角。
她把編劇的職業生涯進行了拆分為:先紮根國內,把影視製作行業的科學知識吃透;接著利用子公司的網絡平臺,作出一部能院線的影片。“最終目標是設立他們的工作室,做他們想做的影片或該遊戲,或是VR、AR。”王鈺媛說。
“但是我又無法回到白俄羅斯做影片。”張蒲中天說。
在北京讀完專科後,即使討厭影片,他去英國薩凡納藝術學院讀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本科生。大學畢業歸國後,劉天力想做編劇、拍影片,而這件事比應付相親還要難。
“像李安編劇那般厲害的人太少了,對許多人而言,返回他們人文的根基、沒有人文認同感,很難作出好的東西。”劉天力說。而歸國後,他和好友在甘南拍了一部叫《风行草偃》的影片,現階段正在中後期階段,順利完成後打算投一些國內的影展。
王鈺媛之後拍的那部同性題材的影片叫《沄沄》,較之在影展拿獎讓她更有成就感的,是一個極少數主義者的聯合會即使片子找出了她,請她去一個高峰論壇做分享。“我覺得我通過電影,為某一個族群換句話說某一個社會議題,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重大貢獻。”她說。
留下來,發生改變那個行業
接下來劉天力想寫一個類似於《我不是药神》方向的類型片,想在故事性和豐厚性上做許多看點。但另一個難以忽略的問題是,把他相片放入人民森林公園相親角的雙親,依然希望他能去大子公司、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趙依銘專科在洛約拉馬利蒙特學院讀了影片電視節目製作,當時要自學所有與影片電視節目有關的各個工種的專業課程,但決定做藝術,是在大二那年的暑期。在Netflix《马可波罗》的片場實習,趙依銘第二次接觸到城市化的製作程序和行業裡真正做設計的人。
給朋友拍戲,千萬別酬金,甚至有時候還要他們搭錢,但張蒲中天覺得,能和編劇一同成長,從前期陪伴到中期攝製再到中後期出來,那個過程很關鍵。
更具體的方面,在國內的攝製常讓他覺得“沒必要那么客氣”。在甘南的山腳下攝製時,片場的人都抱怨天氣情況的寒冷,他醒來之所以沒有感覺到熱,是因為身旁一直站著一名場務同學、拿著黑旗給他遮了三個多半小時。“受寵若驚。”劉天力說,在國外小學生拍戲的這時候,我們都是公平的。
她覺得英國影片學院的那套控制系統,更多的是想把人打導致整個城市化影片製作程序裡,一顆符合要求的螺絲釘。但歸國之後,在做的工程項目一直在延遲,最合適的工程項目還沒有碰到,英國的自學和實踐,一時間找不到充分發揮的地方。“當時是有點兒灰心的。”她說。
他時常想起大學畢業後工作的那幾年,每晚去帝國大廈旁邊的一幢樓房裡上班,下班後就去二十三街裡的一個書店看書,回來後看許多影片,“這個這時候很充實,我似的從小到大都沒製成過什么事,想把攝影這件事一直做下去、搞好,一輩子只做攝影。”
即便是方法論科學研究的專業,也會被派去列寧格勒影片製片廠或是聖彼得堡影片製片廠實訓,做許多製片或是策畫的工作。他發現編劇是實幹出來的,得多在劇組,多實踐,光有方法論知識一點用都沒有。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