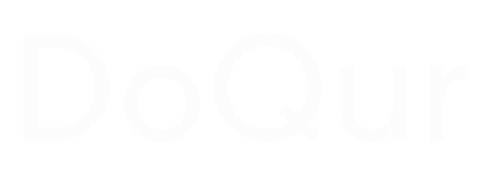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我的姐姐》文學男孩境況真實錄丨良知是幸福產品品質,亦是倫理枷鎖
03 一個更讓人反感的結局,才是影片進行的文學男性困局展現
好似熒幕上的整部電影炒著“男性”議題這一熱門話題,卻又刻畫了一個“為愛犧牲的妹妹”,來維護和發揚“男權管理制度”。
但並非這種的,絕對並非。
當男性和女性都指出安然的宿命是一種悲哀之時,文學女性的境況才真正地開始被理解和共情。
現實生活中,敵不寡眾,男性的自我追求被那個世界壓制著,她們的宿命選擇是被動的。
這色調像是一抹安然內心深處遊離在在紅色綠色之間的理智,模模糊糊說不清道不明的悲哀之色。
同時,《我的姐姐》中也有一個男性族群的發展史切口:影片中滿篇男性皆悲劇。每個男性都被無盡的壓迫與零星的生活溫暖哄著讓步了他們的每一個選擇。姐姐如此,這個一定要生下他們小孩的女患者如此,安然亦如此。
01 安然:一個對世界又恨又愛的男孩
她來自發展史性的壓迫,想要突破發展史,而當她“浮出了發展史熔岩流”時,卻不知該往何方走。
她恨雙親重男輕女,恨所有人都要求她犧牲自我,恨自己周身的世界也這種酬唱著這些不公平的壓迫。
這就是安然陷於的迷局,她無法徹底抵抗,也無法就此讓步。
哥哥沒什么錯,只是個才剛喪失雙親護佑的孩子。她難以讓哥哥為的是不耽擱他們的前程而自我犧牲。
鎖住安然的便是“良知”。
《我的姐姐》整部影片中最有價值、也是其成功之處是:它在觀眾們中種下一顆種子,讓看完影片的人都真切地感受了一遍影片書寫的這段文學男孩深陷迷局的彷徨和悲哀。
居然,他們的計劃被突如其來的不幸全盤打翻,雙親突然車禍逝世,留下一個哥哥要她來扶養。
但深入思索,便能發現,此種期盼只不過是與電影本身的“實錄”功能相悖的。
她憎恨那個世界,憎恨為的是生哥哥而讓他們裝瘸的雙親、憎恨捉弄他們的兄弟姐妹和偷看他們泡澡的姑父、憎恨憎恨要求她犧牲他們理想的倫理要求、憎恨那個世界對男孩的要求和明確規定。
這時,“良知”是一種“幸福的產品品質”的同時,也是一個“枷鎖”。
02 怎樣選擇?或說,沒得選擇
安然一定是她是有自我意識、想抵抗不公平且正在抵抗的人。
《我的姐姐》刻劃的安然才展現出了男性意識覺醒謎局之中絕大多數男孩真實的境況。
她揹負著“長姐如母”的倫理壓迫、揹負著急切想要實現的自我理想、揹負她不願宣稱的內心深處對哥哥的憐愛、揹負著才剛失去父母的劇痛……糾結,彷徨,她陷於了反覆的自我叩問之中。
這一狀態具備典型性,展現出的是文學想要擁有他們獨立人生、抵抗重男輕女的原有倫理社會秩序的男孩的現狀。
當我們談論善與惡這一倫理話題的這時候,我們要清晰地曉得,“善惡懲處”是在維護著一套價值觀之下的一套社會秩序。
“被動”是整部影片的主色,正如這部電影的主題色,似藍非藍,讓電影瀰漫在一個男性想要突破性別束縛卻陷在馬路上沒有去處的茫然之感之中。
她難以讓他們顯得可恥,她他們的價值觀念難以容許她作出道德觀念下“喪盡天良”的行為。
世界還是傳統男權的,而她做為男性,卻想要更多發展史上男性們所沒擁有過的自由和獨立。
較之刻畫一個觀眾們期盼的具備壯烈悲劇性的、更讓人憧憬的“女英雄”的空想形像,影片的立場冷靜剋制,用清爽的立場——一種合乎常人生活的立場——記錄了絕大多數男孩真實的當下境況。
人物在影片中滿篇窮困,結局也逃不過迷局困苦。
這部電影都在為此種看似無事的悲哀流著啞然的眼淚。
根深蒂固的“良知”和對倫理抨擊、倫理殺害的絕望脅迫著“有良知”的她被動地作出每一個選擇。
可她終究未能這么做。
安然的理想已經被哥哥耽擱了一次,她絕不能接受第三次,但是或許全世界都在要求她必須要養他的哥哥。
觀眾們看見這種的結局,有的為妹妹的讓步而憤怒,有的覺得妹妹為哥哥犧牲很敬佩。
這是社會對人的要求,同時也會化為現代人對自我的要求,這種的控制系統之下的彼此間尊重就可以讓社會形成向心力。
姐姐對他們有恩,是一名為的是包含他們在內的夫妻倆犧牲了他們人生的男性,安然沒辦法不感恩,沒辦法絕情地否定她一生的價值。
而且難以拿走她的哥哥,難以拿走她心底的“良知”。
男性的宿命延宕至安然,影片給出了一個留白的、讓觀眾們思索的結局。
她最大的心結就是雙親的偏心。假如雙親徹頭徹尾地對她不太好,她反而輕鬆了。
只是當新的倫理觀念控制系統和評判控制系統創建以前,她想兼顧自身理想和個體倫理的心願與那個世界是錯位的、不適的。
但她也愛那個世界,那個世界也給了她許多溫存:姐姐以一腔正直無私地把她自小養大、父親將惟一的房產寫上了他們的名字、母親柔情地給他們洗頭髮等點點滴滴流露著愛的過往……
這種認為安然或許也是一個原有的“重男輕女”社會秩序的維護者。
所謂維護男權管理制度,是誤讀。甩給觀眾們引起的言論的層層浪花,才是影片留白的真正表意空間。
在這種一個愛恨摻雜的世界中,她的理想和尊嚴被無情地侵蝕,她的選擇被他們批評著、被別人批評著,無處放置。
把一個他們沒見過幾面、搶奪他們夢想的所謂“哥哥”放走,向來獨立有性格的安然能做得出結論這種的反抗。她曾動過念頭,且做過把哥哥拿走的行為。
《我的姐姐》中的男孩安然反感著那個世界,卻又愛著那個世界,她頭上是許多不清不楚地覺醒的男性獨立意識。
是“錯位”令她變為世界的被動者,當她發現了“錯位”時,她也會醒來四面楚歌的境況——全世界都在與她做為男性覺醒的獨立意識作對。
但是她的雙親儘管偏心,卻也嗎愛他們、給過他們許多溫暖。
若想顛覆性的抵抗,必先有足夠多的動因,不然便會讓影片失真,讓“無法信服”毀滅影片的表意。
即使安然絕情地選擇將友情全數割斷,她卻也難以相信她選擇的未來會有什么真正的美好和光明的結局。
影片中籠罩著整個電影的糾結氛圍,便是在書寫此種她與世界的“被靈動”,換句話說就是要書寫一個追求獨立、自由和尊嚴的男孩在現實生活社會中被真愛、友情、索要和贏得裹挾著無法辨別的無力感。
許多人唏噓《我的姐姐》滿篇皆言遭遇戰抵抗,結局卻撲在了男權管理制度的懷中,更讓人極為沮喪。
安然的心願是去上海唸書生活,但是即使家中想要一個男孩,而且只能為的是哥哥犧牲他們的前途。
但安然是個富有抵抗思想的男孩,她不甘心他們這種的宿命,憤然選擇不必家中的錢,他們掙錢養活他們,並準備考研去上海。
叩問之中,恨與愛交織著。
但那些體會都沒有定論,電影給出的立場是留白的。安然安然或許是讓步了,卻又不見得,那個未定論的結局卻或許是給男性的宿命騰出了一筆待續——故事情節的續寫由踏進了電影院觀眾們掌控。
製作者在這一結局設置上,確實沒能夠滿足許多觀眾們期盼看見一個“叛變妹妹”的奇觀的市場需求,更沒有滿足觀眾想在電影中看見“與男權管理制度短兵相接”的“革命”立場的市場需求。
“良知”、“幸福的產品品質”這種的要求是社會秩序的核心評判根據。人人都有“幸福的產品品質”,社會便能平衡厚實。
抵抗這一切,她他們心底過不去這一關。
在此種“被動美感”徹頭徹尾貫穿安然那個配角時,《我的姐姐》給出了一個模糊不清的結局。
安然自小就生活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之中,也生活在一個女性為男性犧牲的環境之下。
文章標簽 我的姐姐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