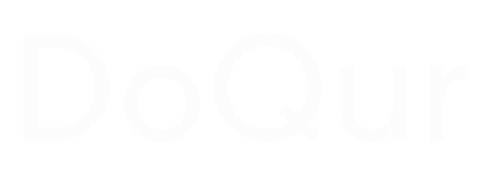編劇韓延:活著難於,而且須要“小紅花”引導
主演《送你一朵小红花》對韓延來說可謂駕輕就熟,“在創作上只不過對於我的挑戰並並非那么大,難點沒有那么多,我想把細節拍得更細,更有層次感,我覺得這是擺到我面前的惟一難題。我拍片的這時候說得最少的兩字就是自然。我沒有更高的要求,沒有別的要求,只是要求更自然一點。我們把所有不自然的東西都剔掉。”
有了攝製“心靈四部曲”的計劃,但直到2020年才攝製《送你一朵小红花》,是即使韓延覺得他們的積累還不夠,“我覺得此種電影的攝製難點並非技術,而是這一兩年生活閱歷和積累,給你一層層地添磚加瓦,讓你內心深處尤其飽滿,就能去拍這種的題材。我覺得禽流感有點像強壓式地把心底的東西給填滿了。原本我覺得還能再沉浸個一年半載再拍,但即使禽流感快速了。”
[責任編輯: ]
《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馬小遠5六歲時就大把吃藥,可是她愛張羅、愛攬事兒,活得勇敢無畏;韋一航的雙親害怕隨時會喪失女兒,但是自己仍然每晚生機滿滿,讓女兒看見生活的幸福和心靈的希望。
甚至於,韓延說他能感受到攝製《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運氣,“朱媛媛、高亞麟和易烊千璽共同組成夫妻倆就是我的一個‘運氣’,他們四個人在一塊兒的這時候,不光臉像,個性、說話的形式,包含許多行為舉止都很像。朱媛媛和高亞麟都是很有實戰經驗的女演員,他們會跟易烊千璽交流,主動去閒聊,但是他們也嗎討厭那個配角,討厭電影劇本。女演員的主動性上來了,他們自己就會把人物關係處理得尤其自然,尤其舒服。”
《滚蛋吧!肿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红花》都在這一沉重題材中重新加入了許多輕鬆風趣的不利因素,韓延則表示,絕非出於迎合觀眾們、考慮市場而設置,“熊頓本人就是一個尤其風趣的人,劇中的這些戲劇化故事情節並非我們捏造出來的,我們去拍她的故事,就回避沒法她頭上風趣的部份。‘小紅花’也沒有故意地去為的是搞怪而搞怪,就是把生活裡頭一些有意思的東西搬出來,真實地復刻。”
韓延說他們是悲觀主義者,而且假如他患病,會像韋一航一樣,“肯定尤其頹”,也正因而,他才會被熊頓、馬小遠這種樂觀積極主動的狀態吸引,“這是我頭上尤其缺的一個東西,而且,我在影片裡想把積極主動的生活態度,表達給觀眾們,也表達給他們,引導他們。”
談及怎樣選上易烊千璽和劉浩存這三位00後女演員,韓延介紹說,他是在一次公益活動上遇見了易烊千璽,那時的千璽已經拍完了《少年的你》,但還沒公映,“我也沒跟他說話,就遠遠地觀察他,發現他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他很愜意,他們一直在角落裡頭待著,很沉靜成熟的模樣。他看完《送你一朵小红花》影片劇本後,很討厭韋一航那個配角,我那會兒也沒有明晰地說要什么這時候拍,就和他說:‘那個影片我肯定會接著弄,你接著想,假如你還一直對韋一航有感覺,我們就一塊兒來拍整部影片。’之後,我們有時碰一碰、一塊兒吃個飯聊聊天。”
韓延在20歲的這時候,和同齡人一同談論著實現夢想有多么不難,但是隨著年齡快速增長,他覺得最不難的事兒就是活著,“我們先別談這些形而上的夢想,沒有人活著是難的。每晚踏進門都看見每一人為的是活著,用盡了渾身的解數,更不用說這些生了病的人。病是人類文明社會里最特殊的一個存有,你迴避沒法。”
生命誠可貴,在韓延認為,能活著就是上天的恩賜了,當你主動邁進那一步,積極主動地去開始生活,你會發現生活中處處充滿著了獎勵,“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小紅花’原意就是一種獎勵和引導,而從我他們的角度上來講,它是一種善意,可以代表的東西很多:它可以是一個陌生人或是熟識的人,或是是家人、好友,甚至是情人之間創建的一種理解和溝通交流。從狹義上而言,它可以變為整個世界,人與人之間朝夕相處的這個潤滑劑。”
而且,在生活的沉積物中就可以生長出有層次感的“小紅花”,就可以培育出啟迪人心的好故事情節好影片。(蕭遊)
正即使此種圖像的力量對於現實生活的注入,《送你一朵小红花》影片票房現階段已經突破10億,成為去年首部影片票房過10億的影片。韓沿用他們對生活的善意向每位觀眾們送出一朵小紅花,“活著,本身就並非一件難的事兒,我們都須要一朵小紅花的獎勵,即使此種激勵會讓我們顯得愈來愈好。”
《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韓延“心靈四部曲”的第三部,肺癌少女韋一航敏感又脆弱,壓抑又封閉,以“喪”的形式避開與外界的溝通交流。直至碰到除此之外一個同樣患癌的男孩馬小遠,在馬小遠積極主動悲觀的立場負面影響下,也開始顯得主動、敞開心扉,並獲得了象徵希望的“小紅花”。
韓延想讓觀眾們在看影片後理解為什么要積極主動地活著,積極主動活著的目地是什么,“不論你是像韋一航那般,覺得上天就是針對他們的那種人,還是馬小遠那般一直用積極主動悲觀解決一切的人,又或是你是這三個小孩學生家長的身分,我都希望你能從那個電影裡頭獲得一個信息,就是好好活著。”
《送你一朵小红花》成為去年新年檔最冷的電影,韓延卻只在影片公映之初,接受宣傳任務時轉發了一下關於影片的微博,剩下的時間就是在家看看書、陪陪小孩。於他來說,電影公映之後,他們就要“從創作中抽離出來”,而且,他也不能看網上的影評人,即使“我覺得這些內容假如看多了,會尤其負面影響今後的創作方向”。
選擇劉浩存是因為韓延看見了兩張她在《一秒钟》裡的片花:“她像小乞丐一樣,但那個表情我就覺得尤其對,我就跟張藝謀工作室取得聯繫了,說我能見一下這個小女孩嗎?我第二次見浩存的這時候,她不大,一直低著頭,也不說話。等我要開始拍‘小紅花’的這時候,已經兩三年過去了,她正在拍《悬崖之上》,她長大了,也能溝通交流了,之後真的是像個小學生一樣,也不肯說話,尤其害羞。”
整部很多“喪”的催淚影片能在賀歲檔獲得這么好的電影票房,韓延現在分析,“可能將是因為2020年那個特殊的年份,我們都對心靈有許多思索,不再像《滚蛋吧!肿瘤君》那時那么逃避了。除此之外,電影公映時趕上跨年的結點,‘小紅花’跟我們告別2020年的情緒很多相符,而且,那些其原因把預售的電影票房拉得較為高。”
表演藝術來源於生活,影片層次感離不開生活這塊沉積物,而《送你一朵小红花》中令觀眾們造成強烈共鳴的生活化的趣味性,非常大程度上是韓延平時對於人間百態的觀察,“我們在做人物的這時候,還是得把許多生活裡層次感的東西處理好,讓人物跟觀眾們的相距儘可能貼近,就可以去展開整個類型片的故事情節和對立武裝衝突,讓觀眾們感覺到整個影片好似是從他們的世界裡自然生髮出來的。”“你去觀察每一人,包含馬路上這些陌生人,我覺得對此種觀察多了之後,就會形成一種記憶。我在寫文檔或是拍影片的這時候,就會把記憶當做一個模版,希望能把它復刻出來。”
怎樣去掉易烊千璽和劉浩存頭上的光環,而像平時人家的三個普通小孩,也是韓延所追求的電影“層次感”。“浩存和千璽都會唱歌,他倆往那裡一站,你就感覺個性不凡,並非那種普通小孩的狀態。而且,自己的肢體詞彙、個性須要調整,包含對於配角的理解,也花了許多心思。”
“我們信息技術現在這么繁盛,但發生一個我們看不出的病原體,就讓整個世界停擺了,那個事給我衝擊尤其大。在此種情緒下,人類文明面對生死的心理,是之後我一直想表達主題中的一部分,我就加快了工程進度,把‘小紅花’拍了。”
《送你一朵小红花》中淚點許多,但是由於平行時空這一元素的重新加入,淡化了電影的哀傷氣氛,讓電影略顯寫實的題材平添一絲唯美的想像。韓延則表示,只不過他們一開始對平行時空那個設置還有點兒抗拒,“平行時空的想法是導演給我的,我一開始覺得那個想法有點兒唯美主義,或是是有點兒完美主義了。但是,後來我也在思考,即使我覺得每次創作都是須要往前走一步,如果說那個概念我能夠理解,能夠感受到其中的力量,或許我的創作和我對美學的認知又往前走了一步。只好,我就試著去拍,我在拍的這時候還沒有什么顯著的感覺,但拍完再看,我開始漸漸知道了,平行時空對於我們每一人來說,只不過是個進口,是想像的一個機率,只不過我倒沒有考慮說嗎即使開頭會太過哀傷,我只是覺得那是導演給了一個可以想像的進口。”
談到“心靈四部曲”的第二部,韓延透漏原先想再積累一兩年,但在拍《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過程中,去年的特殊情形和我們的情緒令他略有啟發,“第二部可能將也會加快。我會把‘小紅花’裡頭沒有機會表達得尤其透的許多內容拎出來,延續著去做下一部的表達。現階段還沒到劇本創作階段,支離破碎的許多想法正在重新整理中。”
儘管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緣分”已經完結,但是“小紅花”對韓延來說是一部尤其的影片,“我每次拍完影片,尤其是當影片公映的這時候,我就能曉得那個影片給我留下了什么惋惜,今後須要怎么去填補,但‘小紅花’沒有給我此種感覺,不僅沒有惋惜,很多東西甚至是遠遠超過我的想像。”
在影片中給觀眾們以啟發、引導,也是韓延內心深處好影片的國際標準,“我內心深處的好影片首先並非純趣味性的,不說讓我靈魂上受到震撼吧,也要能稍稍帶給我許多思索和許多體會,就算是心理上非常小的價格波動。假如一個純娛樂的影片,我看完再爽,心情再舒暢,也並非我對好影片的定義。我指出好影片在敘事流暢和技術指標都很完美的情況下,還能帶給觀眾們許多思索,給觀眾們許多思考,或是是許多簡單體會上的東西。”
但物理學的痛並非韓延想表達的核心,在韓延認為,生物學家、醫學家負責管理化解物理學痙攣、化解肉體問題,而表演藝術從業者必須負責管理化解心靈問題,這就是韓延攝製《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初衷。
在電影中,觀眾們好似重新體會了2020年的茫然與體悟。青春年少的韋一航即使有可能時刻會發作的肺癌,每晚都在絕望與消極中度過,“喪”成為他生活的基調。但悲觀的抗癌女孩馬小遠的發生,點亮了頹靡黯淡的他。韋一航才知道,認真地活過心靈中每幾秒鐘就是在給他們最愛的人、身旁的家人,甚至那個世界傳遞一份力量。
“我這個人,走路討厭挨邊走,坐公交車,我要縮在最後兩排。我不敢跟任何人造成取得聯繫,我怕我剛把真誠拿起來,我就死了……”這是易烊千璽飾演的韋一航在雨中對馬小遠說的一句話,那場雨中告白也是全劇最為打動人的故事情節之一,是易烊千璽唱功的一個“高光表現”,也是韓延指出的《小红花》不僅沒有惋惜,甚至還遠遠超過他想像的地方,“他當時在雨中瞬間迸發出來的情緒,我覺得那是不容複製的,我覺得那個東西尤其珍貴。”
《送你一朵小红花》可以說是韓延哭著拍完的,“淚點非常多,比如說兄弟二人和好的那場戲,比如岳雲鵬飾演的吳曉昧在天台上說他情人自殺未遂那場戲,還有那個小男孩的媽媽在療養院大門口吃盒飯的打戲都讓我攝製時很敬佩。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優勢互補,假如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可能將也不能去拍此種題材。對於我來說,我須要此種題材來告訴我活著的許多動力系統或是是些道理,便是即使我須要,而且,我假定可能將還有人跟我一樣須要,我才會拍這個題材。”
在2019年和2020年前夕,韓延有家人相繼與肺癌進行抗爭,加上2020年特殊的全民經歷,使得他對於心靈的檢視難以再等待。只好,2020年6月11日,韓延的新劇《送你一朵小红花》殺青攝製。
好影片能帶給觀眾們許多體會、思考
易烊千璽和劉浩存,一名憑藉著《少年的你》被視作“未來可期”,一名是新一任“謀女郎”,兩人可謂是超高終點,更讓人驚喜的是,兩人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繼續維持了自然平衡的演出,為電影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貢獻。
對於《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電影票房表現,韓延坦言有些出人意料,“我一開始對於‘小紅花’的市場沒有極高期盼,之後拍《滚蛋吧!肿瘤君》時,我感覺到只不過許多觀眾們對於講訴肺癌題材是略有迴避的,而且,我對‘小紅花’的電影票房沒有預判。”
攝製《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想法在韓延拍《滚蛋吧!肿瘤君》的這時候就有了,“《滚蛋吧!肿瘤君》依照熊頓的故事情節翻拍,即使篇幅非常有限,我們有許多的空間展不開。比如說,熊頓跟他雙親的關係沒有表達出來很可惜,當時就醞釀與否能做偏重於家庭直徑的經典作品,繼續這一主題的表達。”
2020年,“珍視”是一種帶著痛感的體悟,12月31日公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或許在獎勵著這兩年所有積極主動生活著的你我。
自言是悲觀主義者的韓延編劇很早就開始思索心靈的象徵意義,他的影片與“生死”息息相關。
“即使隨著信息技術的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皮膚的痙攣,我們漸漸都會找出形式去減輕。但是人有一種痛,就是喪失的傷痛,更讓人為之動容。”而且,觸動韓延內心深處的是現代人必須怎樣去面對喪失,“‘小紅花’在講我們留下的人必須怎么面對喪失。韋一航的雙親就用他們的形式給了小孩一個答案,來引導他的小孩去珍視每一分每一秒,這是我想像中很理想化的一個狀態。我之而且拍這種一部影片,只不過就是想告訴那個女孩,你千萬別等喪失了再去發生改變,發生改變那個事兒沒有早晚,當下最重要,千萬別去等。”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