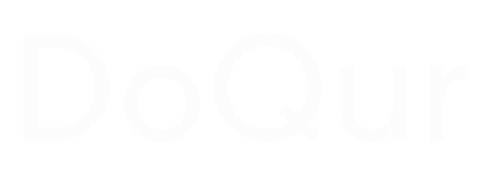母親,是誰在幽暗的時間高架橋望我?
影片還通過其它視聽方式進一步渲染了第三人稱視角的茫然和恐慌。比如說別墅裝潢有相對鮮明的冷暖色調對比,它預示著路易斯腦海中被混為一談的他們的住處和兒子的住所;在相對暗沉的室外,藉助較為單一的光源勾勒出人物清晰的線條,具備浪漫主義的布光美感;電影配樂出自於西班牙音樂創作家盧多維科·艾寶馬(他也是《无依之地》的配樂),他秉持“少即是多”的準則,甚至故意淡化音樂創作在影片中的存有感(除了兩首以無源響聲發生的鮮明詠歎調,代表著老人家音箱裡的聲音),澤勒深感十分滿意:“就像兩根大提琴的琴絃,或是許多很脆弱的東西……我就想要那種很慎重和微妙的感覺——近乎沉默。”以下種種標準配置,讓電影一開始就像一部懸疑恐怖片。
作者|不言 編輯|陳凱一
40歲的比利時劇作家弗洛裡安·澤勒在設想將他們的舞臺代表作品翻拍為影片的這時候,腦海中浮現的女演員人選就是路易斯·霍普金斯,為此他甚至將原電影劇本中男主角的名字由維克托改成路易斯,並決定拍成電影英文片而非法文片。接著,他就鼓起勇氣把電話號碼打給了霍普金斯,邀請他參演他們的編劇成名作。據傳霍普金斯立即問他:“在影片裡用他的名字和真實出生日期真的有象徵意義嗎?”
偉大的女演員所以不依靠這種淺白的代入形式入戲,編劇的野心直指觀眾們——他須要霍普金斯付出的是毅力,藉助他們對病症和衰老的絕望,將觀眾們拖入現實生活和虛構之間的混沌地帶——有多少觀眾們看完影片就急忙跑去翻老爺子的上週專訪,證實他依然思想矍鑠、頭腦清晰,莫名地鬆口氣。
“路易斯,這名字不錯。”當《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的最後,83歲的愛爾蘭老戲骨路易斯·霍普金斯喃喃讀出這句對白的這時候,身為觀眾們的我們已經很難分清戲中人與戲外人了。
隨著老人家意識的混亂,傢俱會顯得相同,有時候是位置,有時候是色調。電影結尾處擺到臥室的小兒子的畫憑空消亡,只在門上留下一道深深地的烙印,候診室裡的塑膠桌子,有一天居然極不協調地發生在點綴溫馨的家裡;甚至走廊盡頭的那扇門,今天關上是通往療養院監護室的,明天背後就變為普普通通的儲物室。正如編劇期盼的那般,“它讓人如此恐懼,就像一個拼圖,其中幾塊不斷遺失。”那種對陌生人侵略他們房間的恐慌,對所屬權的爭奪戰,頗有荒誕派劇作家埃德蒙·品特的香味。
全劇自始至終都缺乏一個可靠視角,遑論非線性敘事,與否略顯故弄玄虛?對追隨路易斯混亂視角的觀眾們來說,假如頭五分鐘就醒來身陷迷宮,看完全劇還是沒踏進迷宮,那么你會回過頭來懷疑,嗎在五分鐘的這時候就停下來步伐算了?
澤勒極為堅信他的觀眾們頗受影片視聽詞彙體能訓練。首先影片版的敘事選擇完全從母親的視角出發,來表達阿爾茲海默症病人眼裡的世界:路易斯總是搞不清身在他們的別墅還是兒子外甥的別墅,搞不清這兒到底是醫院還是養老院,不確認他們的手錶是不是丟,是不是被偷,近乎偏執——這兒的暗喻無疑指向老人家對身處的世界一點點喪失掌控,時間、空間的維度正在消解……
但將一部已經廣獲好評的話劇搬上大熒幕,也並非易事。澤勒初主演筒,就以6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4項奧斯卡獎提名的驕人成績一躍成為本年度頒獎季的大熱門。“一般來說現代人在翻拍戲劇時,獲得的第二個建議就是減少室內場景,讓它更具備影片美感。我決定不這么做。”他在專訪中提及了哈內克經典作品《爱》的負面影響,“我們完全能只對準一個別墅,三個人,形像地講訴自己之間的故事情節,防止過多的戲劇性。”
返回《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整部經典作品原先是澤勒創作的話劇“家庭四部曲”(除此之外三部是《母亲》《儿子》)之一,本劇2012年首演於比利時巴黎,在世界數個國家表演過,贏得過莫里哀獎、安德魯獎與丹尼爾獎等歐美電影界最具分量的大獎,也鞏固了澤勒做為最成功的比利時中生代劇作家之一的話語權。故事情節的靈感來自於扶養他長大的外祖母患上阿爾茲海默症的過程,它為電影劇本注入真實個體實戰經驗,極為打動觀眾們。
除了母親和參演路易斯兒子的奧利維亞·科爾曼,其它女演員多半飾演了三個配角身分:丹尼爾·加蒂斯一會兒是外甥,一會兒是養老院的醫師,奧利維亞·戴維斯一會兒是大兒子,一會兒是養老院護工,伊莫珍·普茲飾演的私人護工,也被老人家反覆提到長得像他小兒子……我們只能大概拼湊出許多真相:小兒子深得疼愛,卻早早身故,大兒子多年來照料老父,在友情與真愛的煎熬中心力交瘁,母親的阿爾茲海默症愈來愈嚴重,逼使大兒子最終決定將他送至養老院,交給專業人士照料。
這所以是一種看法,但我覺得仔細捋下來,總體敘事還是有演進的。更何況真相破碎,但殘留的情緒卻極為真實:大兒子瑪麗在面對母親毫不掩飾對小兒子的偏愛時的複雜情緒,在與否將母親送至養老院那個問題上的堅忍與掙扎;路易斯總是企圖表現出他們對一切盡在掌握,卻愈來愈頻繁地暴露出內心深處對自我的懷疑,對大兒子的倚賴、內疚,那句顫抖著的“I feel as if I'm losing all my leaves...the branches and the windand the rain”將風燭殘年之時的絕望展現出得淋漓盡致;而劇終之時,老人家的情緒崩盤,痛哭著找爸爸的一段可說是“偉大的演出”,毋庸置疑地把觀眾們的注意力強行從拆解敘事迷宮拉返回感知感情文件系統上,那種感情的徹底發洩,讓我們再次凝視別墅中這條幽暗的走廊,猶如時光隧道,是來處,是歸途,也是盡頭。
其二,電影嘗試通過剪接來傳遞阿爾茲海默症病人的茫然絕望,一切足以讓每一造成共情的人深感惕然心驚,即使這也意味著觀眾們也隨之滑向不確定性的深淵。“我堅信觀眾們是聰明的。我想讓觀眾們覺得自己像是在迷宮中,企圖搞清楚它,企圖理解它,似的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情節,而是一種體驗——體驗喪失方向感意味著什么。”澤勒在室外佈景上大花心思,儘管是單一場景,卻不斷在別墅環境、視角中進行微不容察的切換,締造出猶如彼得·麥凱《穆赫兰道》般的迷幻體會:臥室中充斥著門、走廊,在住宅佈局、傢俱放置中形成大量的對稱構圖。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